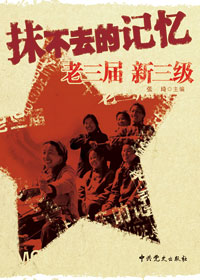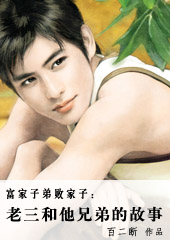老三届朝歌狂飙-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村的阶级斗争情况、文化革命进展情况。
晚饭后,北京来的红卫兵召开全村批判大会。照例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们跪了一地。拳打脚踢之时,一个老头的帽
子被打落,竟是一个头顶有点秃的和尚。仔细辨认,是涌泉寺的老和尚。几个男学生又想起佛门不许结婚的事,忽生奇
想,为什么不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呢?
散会后,红卫兵们把老僧单独找来训话,问他是否愿意娶妻。老和尚一听,连忙低头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怕做不到就怕没想到。红卫兵小将说干就干,通过村基于民兵,抓来一个守寡的地主小老婆,
先痛斥一番她守寡就是做地主阶级的殉葬品,就是妄想变天,然后给她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大道:与老和尚睡觉。老和
尚虽然封建迷信,毕竟没有产业,寺庙是国家的,本人成份估计极有可能属于无产阶级,顶多是个自由职业者,小资产
阶级,属人民内部矛盾。嫁给和尚,不仅生活有靠,还能改变成份,摘掉地主婆的帽子。
那地主婆吓得只会磕头作揖,恳求饶命。但一切都已经定了。红卫兵一言九鼎,当地的青年后生也想看乐子。转眼
间,和尚、寡妇被反锁到一间空房中。
忙了大半夜,红卫兵小将们心满意足地睡了。第二天,他们顾不上吃饭,来到关和尚、寡妇的屋子。开门一看,哭
笑不得。只见和尚盘腿打坐,不知是睡是醒,寡妇跪在床上,面冲和尚,全身匍匐在床上。两人就这样过了一夜。
刘建敏信步上山,来到涌泉寺,见院内已打扫干净,破烂木块都已经堆到伙房,干年文物最后的用场是燃烧自己,
为人类的生存施放热量。那位第一个向红卫兵表示欢迎的战士,正专心地制作镜框。刘建敏走过去,招呼道:“做镜框
呢?”
艾和平很乐意与女孩子聊天,寺里全是清一色的光棍,烦透了。他指着地上的木块说:“净是好木料,看,那块是
紫檀,那块是沉香,做镜框也算是废物利用。做别的做不成了。”刘建敏欣赏着艾和平的手艺:“真漂亮,放张主席像
挂在墙上,不怕落土。”
艾和平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走,我带你去看看效果。
刘建敏随艾和平走进一间大殿,只见原先供奉佛龛的地方端端正正摆放着毛主席画像。画像放在艾和平刚刚用砸烂
的旧文物拼制而成的镜框里。刘建敏恭恭敬敬朝主席像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随文和平出来。
艾和平一定要送刘建敏一个镜框,盛情难却,刘建敏收下,道了谢,离开寺庙。
25年以后,刘建敏自己的孩子也已经十六七岁,正是她当年大串连时的年纪。她几经沧桑,白发平添,生活中许多
事情早已淡忘,许多东西早已丢弃,但是她一直保留着那个镜框,那个用有干年历史的破牌匾拼制成的镜框。如今的居
室中,家用电器、铝合金镜架,已没有摆旧木质镜框的地方,而且那框刨得很粗糙,实在无法摆在明处。刘建敏把镜框
放在柜子里,每到闲暇无聊或心情不快时,就取出来抚弄一番。女儿奇怪,问她是在干什么,甚至怀疑妈妈另有钟情。
刘建敏对女儿说:
“你还太小。等你长大了,我会慢慢地讲给你这镜框的故事。”
从此闭门读书
1966年8 、9 、10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疯狂、荒诞。荒诞铸
就疯狂,而疯狂的心态又加剧了本已极其荒诞的行为。于是,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荒诞言行在那个年代就极为正常地发
生了,“红海洋”活动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当时,参加“大串连”的部分红卫兵没有被中国大多数城乡穷困的生活环境所震撼,却只对外地城乡与北京的“文
化大革命”形势比较相形见绌而感到深深的不安。在红卫兵人人身着绿军装。人人手拿《毛主席语录》、人人胸戴毛泽
东像章的启示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突发奇想:倘若能把全国变成“红色的海洋”,岂不是“革命
化”的又一战绩吗?
他们要再一次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震动全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航“红旗战斗队”总部下令给“红旗”驻
各地的联络站,要求迅速地行动起来,开展“红海洋”活动。在各地群众和红卫兵组织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时,几天
之内,北航“红旗”战斗队便在全国组织人力、物力将大街小巷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都涂上了红油漆,写上了各种
“革命' 的大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在商店里、办公室里、居民家中,则以红纸为主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在墙上。
许多单位的大门上,镶嵌着”忠“字、向日葵,红太阳等图案。大门两边的门上都用油漆写上诸如”抓革命、促生产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 等标语口号,大门两侧的
影墙上,也一左一右设计了两块语录板,在农村各地,树有红色的大牌坊。许多居民家门上也用漆写上或喷上毛泽东头
像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家中最重要的地方一般都贴上毛泽东的画像摆上毛泽东的瓷像和石膏像。许多单位都在大
门内显要位置建造了毛泽东的巨型塑像。这一时期,各大中小城市的商店、机关、医院、学校、饭店、旅馆等等几乎所
有的单位,连同“破四旧”时改换的“革命”名称,一律被覆盖在红油漆之下。茶店、饭店、百货店、照相馆、五金店、
土产铺都无法从门面上去分辨。连厕所的外墙上也被涂上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
全国卷入了新的一轮“革命”浪潮之中。
北京五十五中初三学生16岁的黄小宝,也卷进了这个浪潮中。
那一年,他像全国人民一样,热血沸腾,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那时,红色已是时
代流行色,是最革命的色彩。红色取代了黄色,成为中国的权贵颜色,而黄色被打人十八层地狱。街上卖蔬菜的莱摊上,
黄瓜也被革了命,改称青瓜。黄小宝出身小职员,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也被小学红卫兵斗得不亦乐乎。他想参加红卫兵
被拒之门外,正愁没机会表现,看见黄瓜改名,灵机一动,便紧跟时代大潮,张贴大字报,严正声明,更名为朱红。
也许是心底依然对“黄色”藕断丝连吧,在同学们纷纷南下江浙、广州串连之际,他却充差神使,踏上西去的列车,
领略黄土高原的塞外风光。16岁的朱红,从书本上读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心向往之。他又读到过,
呼和浩特为蒙语“青城”之意,位于大青山脚下。他决定把呼和浩特作为他西行串连的第一站。
火车上,他结识几个大学生朋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北航红旗”在北京也是一个响当当的
红卫兵组织。其首领韩爱晶是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在司令满天飞的时代,他不称司令,以“北航红旗”总勤务员
自称,取“党和国家领导人,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之意。“北航红旗”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
兵第二司令部的核心,这些西上内蒙古大草原的“红旗”战士,怀着要把红旗插上黄土高原的凌云壮志登上北京开往包
头的89次列车。
下了火车,众人已是精疲力尽,举目四望,更令人心灰意冷深秋时节,应是满山苍翠,这里却是一片灰黄,举目远
眺,光秃秃的山岭没有一棵树。火车站外,看不见繁华的街道商店,只有黄土垒起的土房,收割完庄稼的黄土地。土墙
上不知为什么,用白色石从浆划着一个个的圆圈,一打听说是吓唬狼的。朱红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革命口号、大标语也
多是用白色石灰浆涂写在干打垒的土墙之上。如此冷落,如此色调,与如火如荼的北京形成强烈反差。
“太差劲了,一定要把革命烈火点起来!”一个“红旗”战士说,“把式把式全凭架式”,另一个“红旗”战士援
引群众语言说,“第一步应该把革命的气氛制造出来。”
一行人住进内蒙古大学。第二天大学生们忙着建立“北航红旗”驻内蒙古自治区联络站,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取
得联系。
朱红在学校本是逍遥派,捡了一个红卫兵袖章在北京还不敢带,怕被本校红卫兵撞见,到了黄土高原,料想不会与
同学相遇,便放心大胆地把袖箍套上,招摇过市。他在校园里寻摸了一辆没锁的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去昭君坟转一遭。
破四旧的火焰已经烧过这里,碑毁亭残,惟有庞大的土坟上枯黄的小草,迎着习习凉风,可怜地拼命想挺直纤弱的细腰。
朱红沿石阶攀上坟顶,发现土丘上有几处被人创过的痕迹。想来是破四旧的小将们有心掘坟挖墓,后来又因工程浩
大力不从心,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朱红站在墓顶,远望西下的残阳,感慨一番“独留有画向黄昏”的苍凉景象,转身
朝下走。走出大门,却发现自行车没了。他骂了半天塞外番夷有失教化之类的话,只得迈开双脚往回走。
回到内蒙古大学已经快9 点了,“北航红旗”驻呼市联络站里人来人往,正忙得热火朝天,一打听,原来北京总部
来了命令:为坚决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为建设一个红
彤彤的新世界,世界革命的中心应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东方。中国的大地应成为“红色的海洋!”
联络站闻风而动,立即与呼市大中学校、机关商店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取得联系,召集负责人连夜开会,布置工
作。决定分三步走:第一步连夜刷出标语口号;第二步以最快的速度让主要街道成为红色大江、长河,让主要建筑物成
为红色堡垒;第三步、动员群众自己动手,让红色巨浪涌入胡同小巷直至市郊农村。
会一散,各路人马按计划分片包干,四下出击。第二天人们在上班的路上,从大字报大标语中得知,新节目即将开
演。
据说,苏联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活动经费靠党员交纳的党费。一次,苏共在英国伦敦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
经费不足,会议结束以后,没钱返回俄国。普列汉诺夫找到一个大资本家,由全体代表签名,写了一张借据,借了路费,
才得以回国。说是一年以后归还,但直至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才归还了这笔钱。“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
效法革命先辈,以革命的名义乱开借据。后来,追还借出的财物时发现,其中大部分借据地址不详,查无此人。并非红
卫兵小将个个都是骗子。他们当初签署的借据,用的一般都是红卫兵组织和更改得挺革命的新名字。学校、街道、派出
所的档案中没有记载,当然无处查找。
朱红率领一班人马冲进一家化工颜料商店,以革命的名义借走十几桶红、黄油漆,就是打的这种借据。落款是:首
都红卫兵驻呼市联络站、朱红。一两个小时之内,颜料店内的红、黄两色颜料全被拉走,留下的只是几张白条。商店售
货员认真地登记下借物单位:“鬼见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