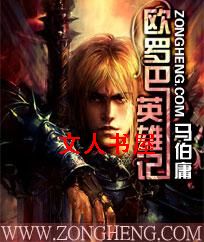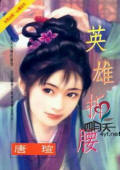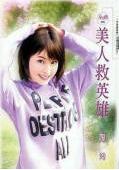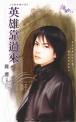��çӢ��-��2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ȴ����ž������Σ�����֮������������㣿
�����ţ��������������������ֱ����ң����Ѳ���鷿�������
һ�뵽�鷿��ȫ�������ĺ����ܣ�Ҫ�����������ٵġ��òΡ�����ȴΪ���Ļ�����ش�л�ˣ����������ǣ���һ���˴˲���ͳ���Ĺ�ϵ���ڶ��������ű��£������鷿���������ò�֮����ʵ���ⶼ�������ɣ�����������������Ҫ��ʾ���������ܣ����������Ѷ��Dz���������
�����ܵ�ȻҲ���ס�����Ŀ�ģ�����ϣ���õ������Ĵ������ſ�������һ������̸�����������Ļ��ľ�������·����������ž������䡣��û�в�����Ѳ����ʡ�֣�Ѳ����ʷ�������ݣ��������ܡ������ܶ���Ѳ�������Ǽ����Ҷ���ʷ���ҽ���ʷ����ͷ�������ӹ�������һ����ְȨ�����Ҷ���������ֱ��ָ�ӡ�Ϊ�ˣ����������ί����������Ļ�������������ʧȥ��Ȩ�����Ȼ��ܣ�����Ҳ���跨ͨ�����Ļ��Ĺ�ϵ�����ž��ܹ��������Է��������š�
���������ǽ˸���ʩ�����ž�ר�����ˣ�����������Ľ��顣�������Ļ����������µ����һ����������������ϣ����ű���̸��Ͷ������Ȼ����̸֮ǰ�����ȹ��������
�����˵����裬���Ѿ���ۡ���аݶ��ˡ���������γ�صĺ��࣡���ܻػ��ж���Խ��Խ���ۣ�ʵ�ڲ��ܲ��ݷ�����
��һյ�������û����������Ļ�ϲ���ε��ʵ�����ԭ�����Ѿ������ҵ�ԭ�ࡣ��
���ǣ�������������Ȼ�أ������Ļ������豳��һ�顪��Ҳ���������Ƿ�ǿ�ǵĹ���Ȼֻ�ֲ���
���ϵܣ��ϵܣ������Ļ�����֪��֮�У������ش���������������㲻���ٱ��ˣ���֪������֪����������£����Ǻú�̸һ̸����
������û�д����£����Ļ�����˽��Լ���װһ����켟˿������ȡ������Ϊ�������ٷ���ͬʱ�Ը������౸��ҹ��ʳ�����Ҫ����ҹ֮���Ĺ⾰��
���ϵ�̨�������Ļ��������������ž��IJ��������������ҵ��㽭����ʦ������������ʲô���֣��������ž��ı��˵������͢�;���������ң��治֪�����ĺξӣ���
���ǣ��������ܴ�˵������������˲���ֻ����������ͣ�����������ǰ���ķ��ϣ�����һ������
����Ҫ����ǰ���ļ��ӣ���ƫ���������ʣ������Ļ�������˵�����ҵ�Ҫ���������кα��£��ϵܣ������˵һ˵����͢�����������Щʲô����
��Ī�������������������κ�֮״������������ϯ��Ͼů�������ı������쿴�����ǵ�;��Ҳ�����͵��ˡ���
�ﺬ���̣����Ļ����룬���������ž����IJ����������������ĸ���ת�����룬��;�Տޣ�֪��֪�治֪�ģ������ž����¼ɣ��ص����������Ŷ������������Եס�����δ��֪���Լ�����ðʧ��
����һ�룬��ͷ������ˣ�����͢�;��Ǽ��Ӵ�Щ������˵�����۲ų��Dz����ģ��������㣬�ɵ�������ɫ���ܵ�ʿ�ٵ��ŷ�����͢������������������͢������ȫ�֣��������ˣ��Ǻܸ�����һ�š���
�������Ȼ�����Կڷ�һ�䣿ϸ��һ�룬��Ȼ�������Ļ����Ĵ��ɼɣ�������̽����Ҳ�ѹ֣��˴˳�����û�н�dz������ĵ�����
������˫����λ��ͬ��ֻ����������̽�������Լ���̽�����������ؽؽ�ڱ�����ֻҪ��������������Լ����ͻ�һ���һ���������Ρ�
������̸̸ֻ�������飬�����Ļ���Щ������ɺ�ˣ��㼴�ʵ����������йݼ�į����֪�����Dz��ҹ����
����ʲô����Dz�ģ���һ���˳��ƾơ������Ļ���Ȼ�ʵ���������ʲô��˯ħ��������飿��
��ν������飿�����ܲ������ף�������������Щ�з��Խ���������Ƶ����飬�����˵�������շ���ͳ��˼�����˵����������棬�ı���ϸ���Կ�һ�ۡ���
����������֣������ٷۣ���
��һ˵���������ױ�ʾ��ϲ�������ְ�˵���������ܴ����������֣�Ҳ���ٷۣ����¿�ӡ�ģ�Ҳ�г�������
�����г����������Ļ��������ˣ������ھ����Щ����Ҳ���ò��٣�ȴ��δ�����������������Ǻ����ĺ��飬��ʲô���֣���
���С����μǡ���ȴ����ǰ�����������������죬�ⲿ�����μǡ�˵���Ǵ��Ƹ�ɮ���ʣ�����ȡ��������������ѣ���λ���Ϊ�ĵĹ��¡���
��������֣��ϵܿ��������������
���ҿ��Խ�õ���ֻ��������Щ�ذ������ҽ��ס���
����ʲô�������Ļ��ʣ����Ǻιذ�����
��������������ʱ�¡���
����Ҳ��Ҫ���������Ļ�Խ�����ȣ����ҵ���Ҫ����������Щʲô����
�������ã������ã��������ܹ���ҡ����˵��������q��suu��c��m�������еļɻ伫���˲���Ҳ�գ���
�����ģ������Ļ�תΪ���ɣ���Ī�ǵߵ��ڰף�˵�ϸ���ô���ţ���
�������ǣ���Ӱ���������Է������
��ร������Ļ���Ҫ�����ˣ���������Σ���
���м���һ�Σ�˵��ɮʦͽ����һ�����ȣ���Ϊ���ٹ�������Ĺ�����ר�ų����ɮ����
�������������е������Ļ��ʣ��������أ���
������һ˵�����Ļ�Խ��Ҫ���������������ͽᣬһ�ص��ң����������鷿�м����ˡ����μǡ��ij���������ȡ��Щ�¿̵ġ������š������Ʋݺ��С�����̰������֮��Ľ��飬�ÿ�������ã���һ���������ˣ�ר�����Ļ��йݡ����ߺ���������һ����ʶ����Ϊ�����μǡ����̻ʵۣ���ͬС�ɣ����Բ����καʼ����������ܷ����ĺ�
���õڶ���һ�磬���Ļ��������룬˵�Ǽ����뵽�й��������Ҫ������̸�������ܲ��ҵ�������Ȼ�¹��˼������Ļ���һ�θ������ˣ��������ҽӼ���
���̫�����ˣ������������죬ȴ���ܿ��ǹٳ��������������˽�ң��ó�͢�������·��ںεأ��Ȼ��Թٲ����������������Ҳ�Ǹ�ְ���Dz���ֵ�ã����ܲ�����һ�¡�
����ʵ���Ѳ������������Ϊ���Ļ��Ѵ�������ӭ�˳����������꣡������Դ��������Ƶأ����ź����ܵı�ţ��ܸ��˵�˵�������������飬�Ҷ����ˡ������ٹ�����һ�Σ�������úܣ����⣬���Ʋݺ��С�������˼��Ҳ�ã���������������м��·��С���
���ǣ������������Σ�ֻ�и��˽�ȥ��
����Щ�ٷ۴��棬�����϶�ࣿ��
����Ų��ٰɣ���
�����㾡���Ѽ�������Ϊ�����Ļ�˵������Ҫ�����Ҽ��������֣��������������õģ����³�������
���ǣ����������ʵ�����������Ҫ�;�������ѣ���
���Ļ������ش���Ȼ����˼������Ҫ����Ҫ���ϣ������ܱ������һ�ʣ����˹⾰����ᵽ�Լ���仰�ʶ��ˣ������ע��������š�
���Ҳ����㣡�����Ļ����ڳ����ˣ�����¥�ܺô˵��������������ޡ���
��¥������ެ�ı�š�����������һ�����Դ���Ե������Ȩ��˵������̫������Щ�����ǣ�Ȩ���Ȼ��˽��ᣬ�ֺαط��Žݾ����ߣ��µ��������η��ηβ������ֻҪ����·���Լ����Լ���������ǧ��������ж�������������һʱ��
��һת��֮�䣬������ȫ������˵���������˵ķԸ�������Ȼ������졣�����������Ϲ��������������ң�����ԨԴ������ð������������Ϲ�����ǰ�����������ҡ���
�⻰˵�ù����ûʣ���ʵ�ǡ�������֮��������֮�����ַ������Լ�����ʹ���ɵ�̫�ͽ��ˣ����Ļ������ɼ�֮�ģ�����Խ�νύ����������ļ����ð������ġ�
�����꣬�����Ļ��������ļ�˵��������������¥���Ǻܰ����ѵ��ˣ����ϵ�̨����ͨ�����������������һ������������������������������������Ͼ��ǡ���
����ŵڶ��棬�����Ļ��д˱�ʾ�����������ø����ˡ�
��������а�ο�����������治�ܲ���֣�ֻׯ����ף���ʾ��л��
�dz��йݣ��ڹ�;�л����������˿������Ļ����ν��������Σ������ܲ����Լ������Ǻθо���������������Ͷ�����������꣬��Ȼ��һ���ɳܵ��¡���ԭ��Ϊ���Ļ���̬�Դ���������ȴ����������ؽ�������Ҳ������ο�����������룬������Σ������Ѿ��仯���ˣ��Լ�ί�����ž��������֮ǰ�����ӿ��ܲ���̫�á�һ����ᣬ��θ߷ɣ��Ӵ˿̿�ʼ���͵úúô��㡣
������������������������������������
����������ܶ����Ÿ������֣������ף��ڸ��Ƽ��������ž������ʢ�硣�����רΪ���Ļ����裬�������䣬�������㣬��������������һ��Ϸ���ӣ�����ǰ�ź�
���Ļ������ų�����������Ƣ����Щ�����ǣ��ž���������¡�أ���̬ȴ����Į��ֻ�����ط����ţ��Ȳ������Ļ����㽭����ʹ�����̸���Լ���β������ò������غ����˼��䣬������ʹ����ɫ������������������ϯ���������걸���������ϯ����
��ϯ���ڻ����У�һ������������һϯ�����Ļ��������ž�����������㡣���½̷�������������������һ���ž��������Ӧ�����������ξ��ơ�Ȼ���и����۹������ں����ϣ�����һ��Ϸ�ۣ������Ļ���Ϸ��
��Ϸ���ӽӵ�������Ļ��������ʣ������������DZ�������
���DZ�������
�����DZ����������Ļ������ž�һ�ۣ������ݳ�����ɽ�ǡ��ɣ���
��ô��������Ӿ磿������ͣ������졣��Ȼ���ž��������ɣ�����������
���������б������������͵Ľ�̸��̸���ǡ���ɽ�ǡ�����������һ��Ԣ�ԣ�ս��֮ʱ���Լ��Ӵ���ɽ�У��Ե�һͷ�ǡ��������λ������������֪��ô��������֮�ģ�Ϊ������������������ͷ���ȵ��ǣ�����ҧ���˶�����������������ԡ���ɽ�ǡ�Ʃ�������𱨵IJ���֮�ˡ��Ӿ硶��ɽ�ǡ�����һλ�����ҵ��ֱʣ�д��һ�磬����żȻ������һ�α������ڡ�
��λ�������տ������ֶ�ɽ�������书�ˣ�����ʮ�����״Ԫ����ѧ�����������¡����³��꣬����誵�Ȩ���������¿��������¡�������������̫�ࣿ��ƾ�����α��ʺ�ң���ֻ������Ѻϡ�
ͬʱ����λ����������������������˼��ΰ���Ը���������ƽ�����ģ������ı��غ���ʫ��ʢ�ơ������Ǻ��εĽ�ʿ������������ѧ��ʹʱ����������誣�����������������ȥ���Լ���һ����ֻ�п����ܾȣ���������ݳ�һ��ֽ����������������ֻ�У������֣�����ɽ���ң�Ψ��ɽ���ܾ��ң���
�������ᣬ�Թ���Ȼ�������Ը��߲ţ�ƽʱ��������������ͷ�����Ա˴˲������������������Ǿ䡰Ψ��ɽ���ܾ��ҡ���ȴ������������ģ���Ϊ���Ƕ��������ġ���ñ�ӡ���һ���Ӽ����˿��������Դ�������֮����
��Ȼ���������Ǿ仰�У������ױ�ʾ��������������������У��������Ψ����֮���Ǵӡ������Լ����д˰��գ����Ժ������ɱ���ֱ����誵�˽ۡ��
��誼���ȥ�ݷÿ���������Ԥ�ȱ�ȥ����ʱ��˵�������ذݣ���ϲ������������ӭ�ӣ����ƿ�������������������˵��������Ľ�Ļ������������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