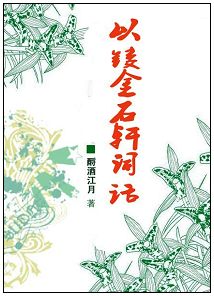���ν�ʯ���ʻ�-��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װ�ڡ��Ķ��������ά���˼�ʻ�ɾ�塷��˵�����ʼҶ��Ծ�Ԣ�顣����ҹ������������Ȼֻ�����ְ��Ҳ����Ⱦ�����߷֡��������꣬����Щ���¡���һ��һ�Σ�һ��һҹ����һ��������д����˲��࣬ȴǣϵ��ʲô�£��Ǵ��˴�������������Ǵ������ϵ�������
������ͷ���������������Զ������ѱ�����ζ����ɲ��֮�䣬�Զ����ѱ�Ϊ���������ݽ���ת����Ȼ����������������Ϣ����˯Ҳ����������˯������Գ��ľ��������ҪЪϢ��ȴ����˯���ǻ��������£����Ǵ��˵����£�����һ�䣬�㽫���˵�ì���������̻�����ľʮ�֡��������һ����̾�����������ӣ���Ҳ֪δ�������в�����֪��Ȼ�����������������ϣ�ҡҡ�ĺ��ѽ������������ֳ��ʣ��ֺ����̹�¥�ʻ����е��������Σ������ĺţ��ʷҷ������ɧ����֮�ţ��̷�ղղС��Ҳ����
��������������δ�ѣ���һ����ˮ����һ�����ᡱ���ش���˵ģ�ֻ��һ�������������������ǣ��ǻ�������ô��
���������ѱ棬����Ѫ�ᣬ������ˮ��
���ģ��������ݡ����ɽ������ǧ��
�������ݡ���������
�������Ӱ��¶�ʮ���գ������ܡ����������ء������ᱦ��ӡ��������ʱΪ�Һ����£��������濪�����꣬���Ű���ʮ�����ӣ�ǧ����飬һ����ȥ��ĩ��ħ�Ī�����֮�ƣ���ʱ�۶ԣ�����Ǭ��֮�ǡ������ˮ��������֮��������б�����òк���ѻӰ���ͬ���٣��������ף���д���
�������ɽ��������ǧ�꣬���ľ���������ͼ˥Ъ���������ã����Ǯ����һ����ǧ����ָʧ��װ������ɳ�����ѵֱ�������������ο�Һ������ۣ�������ĺĺ�������⡣�̲������£���į������������С��������ˣ��γ��ա�ѻ��ռãã���ӽ��ƾ˭���죬���б����
����Ҷ���¡������дʡ��������ٵĴʣ�˵�������ȣ������ٵ��֣���ʮΪ�ʣ���������д��Ԣ�У��Dz���ڣ���������ٱƥ����ν�������Ҳ���������״��У��ɼ�����������һ���еġ������ɽ��������ǧ�ꡱ����ͷֻһ�����֡�һ���͡��֣��ѽ�Ρ��֮������ɣ֮�У��̻����¡��ٿ�����ɽ���������ꡱ�Լ���ǧ�ꡱ�����ǰ���ʷ���ӡ��˼������һ�䣬����֮��ã̬֮�������Ѵ���
������ʱ��������Ȩ�����˵��𣻸ٳ����棬�����������С�һ��ʷ�ң�ǧ����ʡ�֮�ƵĹ�Խ�̶�������ν֮������ʹȫ������Ϳ�����������֮���£��ֺ����弾����죣������Ӱ��¶�ʮ���գ�����һ�Ŷ�������¶�ʮ���գ��ﴫ�����ý����㽻��֮�����뺼�ݣ��ʷ�����̮��������������һ��ʱ�������£���ϵʱ�����ݵ��Ű���ʮ����ǰ����˳���Ρ�Ԫ����������£���ӽ�������㷢�Լ�һǻ�İ����ʹ��
���������ľ���������ͼ˥Ъ���������ã����Ǯ��������һǧ���ˣ���������ն��������𣿻��ǣ��㿴���ˡ���ͼ˥Ъ�������������á��е�̫���ˣ����˸�Ħ��Ϧ���µ�������ǽ�����в�������������ڵ�ʡ��ǰ����ǰ�����ʷ�ķ�˪��һ����һ�����ʴ����������Ҳ��������ʲô��ɽ����ʲô�����ˡ�
���������ţ���һ����ǧ����ָʧ��װ��������������֮��̮������֮�ݡ��ģ���ֹ�Ǵ�أ����д��˵��ľ���̮���ģ���ֹ�ǹ��������д��˵��黳��������ɳ�����ѵֱ����������ƾõ���ʷҲ�����Ǻ���е�ɳ�����ٲ�ã��ɽ��Ҳ�ѵ־�������ı������뵽�˴���������˼���룬�Ȼ��ʧ��
������ͷ���䡰ο�Һ������ۣ�������ĺĺ�������⡱���ͽ���ͷת���˴�ǰ��Ҳת����һ����ˮ����ի��ի�м����Ȼ��իǰһ�ˣ���ˮ��ȥ���������������dz�Ϧ��ˡ�����ο�������������˷���Ĭ����һ��Ѭ�ޣ����������ź�ɽ��ʦ�ġ����������۶��ľ�ֱ˵������������־�������ߣ���˾����۷��ӡ���ν���Ͽຣ�У�����Ϊ�ۺ���ڤڤ��ҹ�У�����Ϊ����
������ͷ��ת���ֻص������ڡ����̲������£���į��������������ܣ������������һ������֧�����Һ�Ȼ��������������ˮ����һ�ס����㡷�еĴʾ䣺������ϻ��������ս���������������������������������𡣡���أ���Ҳ�Ǵ��˵�ʱ�ĸ��ܰɡ��������С��������ˣ��γ��ա�ѻ��ռãã�����������˻���һƬ���棬Ǯ������ֻ��ѻ��ãȻ����ֹ�ǹ����������ˣ����˻�����ȥ�������˥�ϱ�Ӱ��һ��һ�㣬��������ʷ��ĺ��֮�С�
�������ӽ��ƾ˭���죬���б�������������еļ���ѻ��ʧȥ��Ρ�������ͣЪ�����յ�������б����û�������쳤���Ĺ��졣һ��ž��У�����������û�����꾭�ģ���������ߣ������յ������Ŀຣ�����Ķ�������ߣ��֪�������ӡ�����
���壺����������ҹ�Ž�
����������ҹ�Žǡ���������
����������ң������˪�أ����������˾롣���ת�֣�˼���ѻأ����ʲ�����䡣��ʶ�ʱ���������ģ����Ÿ��㡣�����˻��ף�����˿�����ݸ�ܡ���������ƾ��������������������Ω�У���������ͥԺ��������Ļ��������������Ҳ�������ϣ���ȴ���裬��Ī���ڣ����˾��ߡ�����֦���գ�Ӧ������һ�롣
����ޥ�磨���������úţ����У�����ά������������ߣ��ڡ��˼�ʻ�������Ϊ�����������棨�����ܰ���ţ����������������ܹ�֮������˵����ޥ��С�����ԭ�������缸���֣��������������桢÷Ϫ������ʷ����ţ��䣬����ʹ��֮�����壨������Т갺ţ��主����������ѷ����ֿҲ��������֮�ߣ��ɼ�����һ�����ڡ�
�������״����ڹ���ʮ���꣬��������ھ����θ������顣�����Ǹ������ҹ���ɣ�����©��һ���¹⣬�����ѩ�����˽�����˯��������غŽ������������˵��������£������ƿ�����������ҹ����ˮ��һ����£�б�����ҡ��Ȼ��磬������쪣��Ž��庮�������ź��˵��������˺����п�����ʤ�̾��
�����������䣬�᳹ȫƪ����������ң���������֮�㣻������˪�ء���д����֮������������ҹ���������ת��ƣ�롣ֻ�������䣬��һ�۴��⣬�ͰѼ��ڡ�����ʱ�䡢���������������ݵ��˼��¡����˵ij�ా�������Ὣ�ϣ�˼���Ŀ��Ƽ���������δ�ꡣ��������û��˼��ΪʲôҲҪ����ѵ���������һ������ô������һ���Ц��
���������ת�֣�˼���ѻأ����ʲ�����䡱���Ž�֮�����������Խ����Ȼ�θߣ��糤�����֣��������������������ã�������������Խ��Խ�ͣ�����ϿԳ�䣬������ҹ�����Ž����У�ʼ����һ�ֳ���ѹ�֡��ٽ��ţ�����������䣬�������ޣ��������ߣ�������Ȼ���������ŨŨ�����֮�С�
��������ʶ�ʱ���������ģ����Ÿ�©�������ںŽ������ڼ��𣬹����������ž�֮�У����䴫�������©���·�����̫Ϣ������̧����ȥ��ֻ�������࣬�������졣������������������䣺����˿�����ݸ�ܡ����Ľ�ҹ�������γ������Աȡ�
������ƾ��������������������Ω�У���������ͥԺ�����н����ı��ࡣһǻ��������������ƽ�����ͥ���£���Ӱ�β�������������Ҳ�Ǽ��е����ΰɣ���������Ļ��������������Ҳ�������ϡ����������дʡ�˵������������Ļ�����䣬�����̣����������������ϣ��������֮�ʡ���һתһ�һ��һ�ί�����ۣ�����㮻У����˲���Ϊ����һ�����ݵĽ��ޣ�������������˼���˼�����꣬Ҳ�������˽�ҹ�ĺŽǣ�
��������ȴ���裬��Ī���ڣ����˾��ߡ����䣬������ͥ�ޡ���©�ӡ��������裬����ڣ����������ľ��⣬�Ա������㣬������ѻ��*����������ġ�����һ�䡰����֦���գ�Ӧ������һ�롱����������»��������������졣�����ɨȥ����֦�İ������㣬�������˽����������գ���������������뿴����
�����������ɡ�����
�����ɡ���������������
������ҹ������̻�ͷ�������ʹ����������ˡ����״���Ѱ���Σ�ĪЦ����������Ҳ���ܡ��˼��㲡����ճ��̹����ڣ�����ɽ�������ݺ�ء����İΣ������������������ﻪ����ɽ���졣��˭�ҡ�ׯ����齣�������˯������ǧ�������У�һ���������ӡ��ʴ�ˮ��������£����������˲����������ġ�����Ӣ���ᡣ�����ң�������
�������⡶����ޱ�Ŵ���˵������������������û���Ҷ����ĩ���˷Dz���Ҳ��Ȼ����֮ʿ�����������������״ʿ�����Խ��������£�����֬����Ϣ���������������������ļ�������������һ�䣺���ᱲ֮Ϊ�ģ���������֮��ɽ��ٹ�����֮��Ҳ��Ӧ��ʱ�ƣ��������������ԡ��������������״����ٺò����ˡ�����ҹ������̻�ͷ�������ʹ����������ˡ��������ľ䣬һ�����̡��֣�����������������֣�����ȫƪ��������ҹ���磬�����ʹ����Ƿ�Ҳ�������˵�ǰ㣬��Ȼ���������ˣ�
���������״���Ѱ���Σ�ĪЦ�������������ź⡶���������أ������ߣ����˵���¹�����֮�����Ծ�����֡��������ɣ���Ϊ��ߣ����ô��������������ס���ָ������֮��Ұ���ش��أ���ָ�Ϸ֡������й�����ǿ�������ǹ���ʱ��Ż�ľ�Σ�����ǿ�Ϸ�����֮Σ������͢*����֮������д��ۣ����ӷ�硡���Ҳ���ܡ��˼��㲡������˷߿�����ֻ֪͢�������ͣ������ʲô�۹��������֣�����Σ����
���������ճ��̹����ڣ�����ɽ�������ݺ�ء���չһ��ç�Ծ����˵���Զ���������Ÿ裬���ֲ�������һ��ĺ��������ֿգ����������Զɽ��ɡ������뵽ǰ;������ƽ����Ȼ����������һʹ��̾���������İΣ������������İΣ�������������ɪ���У�ֻ�к���ŭ����������˻��
������ͷһת�����д�¡��ﻪ����ɽ���족����ɽ��ת����ʷ����������ããĿ�ã��ﻪ��ʣ���Ȼ�ǽ�ɽһ��ͼ����ȴ����һ��֮�£������������������ޣ��������ޡ�����˭�ҡ�ׯ����齣�������˯���������������桶������Ƹ���������֮������������˯Ү����������˵���������������ڡ�̸Է��������������ʦ��Χ���꣬�����Dz�����볯����춱��������´�֮��������ͽ�Ա�����δ�γ��ˣ��ǸҾ�گ��̫��Ի����������ԣ������к��������һ�ң����֮�࣬�����������˯������
�������֮�࣬������˯�����֮�࣬������˯�������������ģ�������ڵ����͢��������߳����ǿ�����˴����������������������ˣ������������������𣬱�պŨī��������ǧ�������У�һ���������ӡ�����ʯ���쾪�������Ŀ��������˵ġ�ʮ���������ף�����һ�����ж���һʫ�˽������������ս�����ĺ��ƾ�����ù�Ѫ��ͷ��������Ը�����������͢�������ʣ����û��һ���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