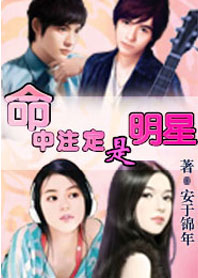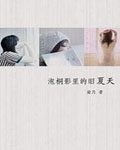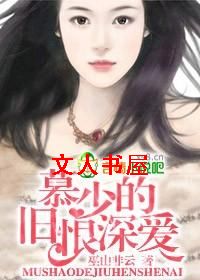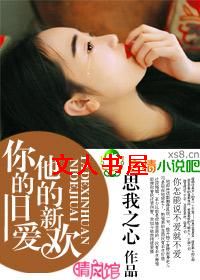行板如歌的旧时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像歌手韦唯,她告诉我小时候她放了学领我出去玩,来到商店看到有卖糖的便问我要那一种,我告诉她“全要”。她很为难地说“我没有那么多钞票。”我就立马往地上一躺。这个故事让我震惊自己小时候是多么无赖啊。
6。我西安的家
三姨妈的小儿子大家都叫他阿民,看上去很有腔调;我在上海读小学时,弄堂里那些比我要大许多的女孩子们显得十分关心他,总是带着一脸诡笑向我刺探他的点点滴滴。我那时小很不理解她们为什么那么关注他,总觉得阿民表哥像个二流子,我从来见了他都是横眉冷对或挑起事端和他拌嘴,当然他不会真的和我吵,只是故意逗我玩罢了,毕竟他要比我大十一岁。
小时候在三姨妈家寄养的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能从照片上模糊地联想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场景,比如我曾在照顾我的“上海呣妈”家摔断胳膊,据说那是粉碎性的骨折,医生说一定会留下后遗症,但是我好像没有觉得有多么疼,到现在也没发现有什么后遗症。模糊还记得当时照看我的“上海呣妈”,她温馨的家和善良的家人;还有三姨妈家阳台上的月季花……
第一次和妈妈回到西安,其实心理上应该是很无依无靠的,虽然只有四岁多,却还是有一些深刻的印象。记得回到家姐姐很高兴,以为有了妹妹做伴可以不再被送到幼儿园全托,可哪曾料到妈妈把我们俩都全托了。现在还能想到姐姐放声大哭的样子,后来我们在幼儿园里住,很是不习惯,记得那个凶神恶煞做饭的阿姨总是很野蛮地往我嘴里塞那些我咽不下去的饭菜和肥肉,搞得我常常想吐,在那里真的不比简爱小时候待的孤儿院强多少。
当时的幼儿园没有什么专门的老师,只是把那些划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下放到那里轮流看孩子。整个管理也是松松垮垮,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小伙伴拿着莲花白的根根在啃,我很吃惊觉得这东西能吃吗?她说可以吃的,后来我趁大家不备便溜出幼儿园,在院子里的垃圾堆捡了一个莲花白的根根吃了起来,那次我得了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记得当时发高烧上吐下泻,妈妈背着我走了四站路来到医学院给我看病,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卖冰棍的我又嘴馋,妈妈不忍拒绝生病的孩子,便给我买了一根,可是一吃又吐了。这场病让我至少一星期没去幼儿园,所以从那时起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这样会得到妈妈格外的呵护,也可以不去幼儿园,不去吃那些让我呕吐的饭菜。
学校的幼儿园就在我们的家属院内,记得有一晚姐姐偷偷带我溜了出去,我们俩坐在我家楼对面的高台上,姐姐指着三楼我们家的窗子哭了:“你看啊,家里台灯亮着,妈妈在啊,她骗我们说晚上系里学习,其实她不要我们。”姐姐伤心欲绝地哇哇大哭,我也跟着嚎啕起来,姐姐很习惯地说到“系里”那也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疑问,因为我妈妈是教师她怎么会去“戏里”呢?后来姐姐很不屑地告诉我妈妈是统计系的。我永远记得家里那盏有着蓝色塑料罩的台灯,因为妈妈总是坐在那盏灯旁看书;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真的不在家,只是为了防小偷开着台灯罢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妈妈并不是去系里学习,而是被系里批斗。
妈妈的家庭出身不算好,又有一个反革命的哥哥,这让她在那些根红苗正的人们面前好像矮了三分,而妈妈的天性与世无争,她对从事的政府部门工作似乎失去了兴趣,她明白因为她的出身问题恐怕是很难入党,也很难有什么前途,所以便想到了做学问。她考上了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在那里认识了我爸爸,他们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分到了北京的一个单位,可是还没等他们去,那个单位就已撤消了。当时他们选择到西安是不想再往北走,因为他们都是南方人。我爸爸是广东潮州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赤道在那里经过。
第一次对广州的印象就是回到西安不久,我们在印尼的爷爷奶奶回国了,我们全家到广州和他们见面。那次去广州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半夜12点在郑州换车,任凭爸爸妈妈怎么叫我我都醒不过来,或者是疲乏得走不动路。还依稀记得这次去广州我们还坐船去了江门,我晕船吐得厉害,基本一直躺在铺位上。到江门是去看我们的一位堂叔,他和爸爸从小关系就很好,长大又一起回国读书,每个寒暑假这些华侨学生都会自发地组成一个旅游团,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每次出游的照片爸爸除了和他的两个弟弟外一定还有这位堂叔。后来文革结束堂叔一家去了美国,现在他好像已经去世多年。
其实更小的时候也去过广州,只是根本没有记忆,只能从老照片上得到证实。正真认识爷爷和奶奶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记得我们又是坐了三天的火车千辛万苦地来到广州,想必当时狼狈不堪如逃荒的盲流,奶奶一见到我们就哭了,并要求爸爸妈妈把我们的衣服裤子扔掉,可能是觉得我们太像叫花子了。
记得奶奶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但是仍然很美丽,她穿着天蓝色带有小花朵的纱织的上衣,下面是一袭印尼沙龙,我傻傻地看了她半天,心里诧异她就是我的奶奶?我当时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觉得她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7。终于见到爷爷奶奶
奶奶不会说普通话,但我还是能够明白她连说带泰国舞般的比比划划所表达的意图。说来奶奶是位英雄母亲,她一共生有12个子女,成活了10个,6男4女。我爸爸排行老三,是男孩子里的老二。十个子女中只有我爸爸一人在国内定居。据说,当年在印尼的华侨稍有条件的都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回祖国接受教育,主要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传承中国的文化。
爸爸是第一个被送回国的,那时爷爷留下了只比爸爸大一岁多的大伯帮助家里打理生意。不能回国读书,这令大伯感到非常不公平。后来三叔、四叔还有小叔叔也相继回国读书,只有五叔没有参加这回国大军。爸爸家的亲戚我只见过大伯一家,还有二姑、二姑丈和小叔叔。
大姑是家里的头生子,但是很早就去世了,从照片上看她很华丽,据说她的儿女们都留学美、加,学成后都并没有回到印尼而是选择留在了当地。
大伯家有六个孩子,他们一家由于当初回中国居住被分成了两半,大伯与他的长女和两个儿子在印尼,剩下三个女儿和大伯妈在澳门定居。我们去广州就是住在大伯家,印象中那房子好大好气派,据说当初他买那所房子才花了8千多人民币。大伯原计划回国定居,不料,碰上文化大革命,据说当时存进银行的外汇只能取出人民币,这让大伯很恼火。后来他的长女又被工宣队押到农场强迫劳动改造,这彻底伤到了大伯的那颗中国心,于是乎全家决定返回印尼。可是,印尼当时的排华政策也不由你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大伯一家是进退维谷只好暂居澳门。后来大女儿和两个儿子陆续回到了印尼,另外三个女儿在澳门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习惯了澳门紧张的生活节奏,便怎么都不愿意回到印尼过传统的懒散、无所事事的日子,大伯妈只好留下来照顾她们的生活。
当时住在大伯家并没有见到大伯,见到他是后来的1980和1981年。我们那次只见到大伯妈和他们的六个子女,爷爷奶奶和我们的小叔叔。记得当时我们被拉到卫生间狠狠地刷洗了一番,出来全都穿上了堂姐们的漂亮衣服,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要妈妈把我们的那些打有补丁的旧衣裤扔掉,可是我们回到西安时发西现它们都被带了回来。
我们在广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整天除了疯玩就是和姐姐吵架,记得当时因为姐姐名字里有“美”字,所以我就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高呼“美帝国主义必败!越南人民必胜!”等等。我姐姐气的直哭,后来大堂姐给她支招,说我的名字里带“小”字,便给我起了个“小日本”的外号,这下姐姐可神气了,她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像电影里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那样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开始我傻眼了,很快就跟她拼嗓门,看谁坚持到最后。大伯的四个女儿很快就加入到我们的战争,老大、老四支持姐姐,老二老三则和我一国。后来因为姐姐十分倔强任性的个性,很快失去民心,大家都站着我的一边,护着她的就成了更有力的爸爸妈妈。
在广州家里的三个男孩没有参加我们的战争,两个堂哥和我的小叔叔,小叔叔的年龄要比大堂姐还要小,当时在广州读中学。记得大哥基本上终日关在自己的房间弹吉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吉他,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升级到动武时,大哥便把我们拉开带我到他的房间,送给我一大把铅笔和糖果,并弹吉他哄我玩。很快我就缠着妈妈也要买吉他,妈妈拗不过我便买了一把四弦琴,我很生气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件玩具,后来倒是姐姐常常弹它,估计也只是为了学新歌时找音准罢了。
8。人生就是聚聚散散
在广州的日子既懒散又惬意,那里除了有宠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亲戚本家们,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冰激凌、雪糕和各种精美的点心;这是当时的西安根本没有的,记忆里西安那时候只有4分钱一根的白糖、豆沙冰棍。西安的点心在当时还有那么一个笑话——说,有个小偷进了点心店偷东西,值夜的大叔顺势抓起一块点心照他扔了过去,小偷应声倒地被点心砸的头破血流。呜呼!可见那点心有多硬。在广州大街上有时能看到像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那样的,烫着大波浪头发、穿着大花布拉吉的时髦洋太太,那可是当时闭塞的内陆城市西安根本看不到的西洋景。还有空气里也弥漫着一种暖融融的、甜甜的花香,多年后妈妈种了一盆米兰,那花的香气总会让我想起广州。
终于我们要回去了,奶奶舍不得我们又是泪眼婆娑,大家也极力地挽留我们,说二姑很快也要来广州,希望能见上一面,可是妈妈推说不能再耽误我们的功课,执意要带我们回去。现在还能记得奶奶送我们到火车站,无限眷恋地向渐行渐远的我们招手;也能记得我们安慰她说一定还会来广州看她。可是,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几年后她驾鹤西去。
当时爸爸没有跟我们回去,而是留下来和二姑见了面,二姑是爸爸最大的妹妹,后来大概是到了1987年,她和姑丈来西安看我们,那是我一生唯一见到她的一次,感觉她是一个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时髦女士,终日都在告诫姑丈不能在外面拈花惹草,姑丈总是无奈地做头疼状回答“知道、知道”。也就在那时二姑突然接到电话说爷爷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有点儿懵,二姑百感交集地告诉了我们一些让我觉得还不如不知道的事情,因为那让我对爷爷的敬爱之心大打折扣。据说奶奶在即将离世的那段日子是非常痛苦的,爷爷公然感情走私,和家里的一个印尼当地的女佣搅在了一起,那女人当时只有30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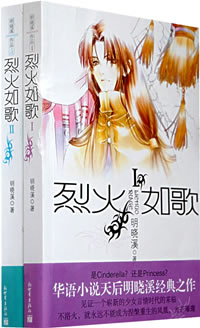

![[网王]岁月如歌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18/1871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