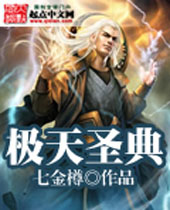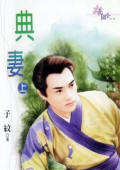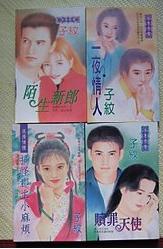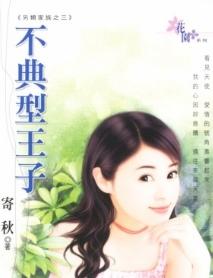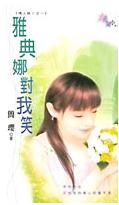米沃什词典-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名:《米沃什词典》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8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生回忆录,呈现20世纪历史文化广阔的精神地图。
1940年6月,29岁的切斯瓦夫米沃什闯过苏军与德军四道防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纳粹占领下的华沙。半个多世纪流亡生涯之后,他才终于重返故乡维尔诺,一座“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与自己的过去重逢,他回到一种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开始为各种历史人物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他自己。
《米沃什词典》就是这样一件替代品。它替代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篇关于整个20世纪的文章,一部回忆录。书中所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网络中活动,相互阐释,相互依赖,并与20世纪的某些史实相关联。≈米≈花≈书≈库≈ ;http://__
“词典”(Abecadlo)是波兰特有的文学形式,由短文(词条)组成的松散文体,文章按词条名首字母的顺序编排。《米沃什词典》是米沃什亲自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与他一起到过人间的天堂或地狱的人,几乎都已去了幽灵王国。本书是对那些灵魂的召唤,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仪式,换取他们的片刻显形。他用词典这一相对客观、抽离、高度浓缩的形式,以平静、卓越的才智,将他的时代丰富层面的体验,浓缩为一个个充满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
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Milosz,1911―2004),美籍波兰裔诗人、作家、翻译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者,“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著作宏富,主要作品有诗集《冬日钟声》、《在河岸边》、《三个冬天》、《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无法抵达的土地》、《拆散的笔记簿》,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自传体小说《伊萨谷》,回忆录《故土》,日记《猎人的一年》,译著《圣经诗篇》、《五书卷》,等等。
书摘正文
译者导言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一
据波兰诗人彼得佐默(Piotr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InternationalPrizefor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作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20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客》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词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2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尔伊瓦斯克(IvarI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3这种情况没有到过东欧的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党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事务一等秘书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没有名字的城市》)4—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Valéry)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莱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5
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评,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人提出了指责:“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Polish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6
第2节。
二
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称维尔纽斯,意第绪语称维尔内,俄国人过去称之为维尔纳。维尔诺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属于波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为立陶宛首都。该城始建于10世纪,一直是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混居的地方。米沃什虽然生于基日达尼(Kiejdany),但他是在维尔诺长大和受的教育。他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中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四十座天主教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城市的周围绵延着山岭。老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丘。城市上空凝聚的云朵犹如城中的巴洛克建筑。米沃什曾先后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住过,但是说到城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尔诺。是维尔诺建构了他有关城市的观念。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谈到过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7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米沃什不仅熟悉他那个时代的维尔诺,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密茨凯维支时期,维尔诺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它也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此外,它还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认为,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其实是波兰庄园文化的延伸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庄园少爷(他个人的经济情况在维尔诺时期和巴黎时期都不好),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
但是维尔诺带给米沃什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米沃什以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集中的反映。可以说死亡对于米沃什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因此才会在诗里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逃离》)死亡和发生在波兰、苏联及东欧的事,把米沃什塑造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般不会被看好。读者和批评家一般会追究一个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动人,其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结构是否精彩,但米沃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成为诗人中的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对苏联的赞颂和对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掩盖,令米沃什愤愤不已。由于他在波兰和在法国的经历,这个早年政治上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右派,并且称左派为“乌合之众”。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恰恰是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后,才开始了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第3节。
可能有两个因素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流亡:距离使得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距离滤除了他与维尔诺的日常纠缠,使得维尔诺更容易进入书写。远景中的城市或许比近在眼前的事物更适于被观看。想想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这个问题便很好理解。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米沃什心里装着维尔诺,并不等于国人所说的“怀乡病”,即使米沃什在流亡中思念家乡,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了自己的乡愁,从而避免了对于家乡的美化。这样,他便赋予了维尔诺以更大的历史想象、道德想象和形而上想象的空间。维尔诺一方面担当起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社会生活时所不可或缺的他者。俄国批评家托马斯温克罗瓦(TomasVenclova)曾经指出:“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诸省份以一种唤起的力量出现在(米沃什的)诗歌中,就像马丹维尔和贡布雷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8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的第二个因素,大概是波兰人对历史的屈辱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来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谈起这个问题仿佛感同身受:“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们所知道的大屠杀。”9这种历史的屈辱感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他写道:︴米︴花︴书︴库︴ ;www。7m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