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郭沫若北伐时期当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1949年后又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副总理,说起来,一生也算是“出将入相”了。1949后,跻身于那些工农出身的、枪林弹雨中熬出来的将相之列,不知郭沫若自我感觉如何。至于那些将相如何看他,“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中倒是有所透露:“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郭沫若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着特殊的交情。在现代文人中,除柳亚子外,只有郭沫若与毛泽东有着唱和关系。而郭沫若的成为“党喇叭”,很大程度上就是周恩来直接铸造的。对郭沫若,那些工农出身的将相们表面上应该是很尊敬的,但罗点点的回忆告诉我们,他们对郭沫若内心却颇有鄙薄。“脱党”一类的议论,罗点点这样的孩子能听到,说明他们的父辈在议论郭的这类“重大问题”时并无多少避讳。他们不太避讳地非议郭沫若,则说明郭沫若实际的政治分量并不像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么重。郭沫若的孩子与罗点点们是同学和游玩伙伴,那些将相们对郭的议论完全可能传到他的耳里。听到这样的议论,郭沫若该有一份惶恐吧。罗点点回忆录中又写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所谓“为曹操翻案的戏”,即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郭对历史剧情有独钟,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则是他编撰历史剧的基本原则。发表于1959年的《蔡文姬》显然也是为其时的现实政治服务的,也仍然是郭沫若这支“党喇叭”里发出的声音。但罗点点的回忆录让我们明白,对郭沫若的这种表现,那些工农出身的将相们并不打心眼里佩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郭应该拒绝做“党喇叭”。对于那些有着某种程度的独立立场、对现实发出批判声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痛恨的。四十年代的王实味和五十年代的“右派”,都让他们痛恨。但像郭沫若这样一心一意地做“党喇叭”,又令他们瞧不起。罗点点说到,由于受父辈的影响,他们这些孩子也时常在谈到“郭老”时出言不逊,并说:“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罗点点的父辈们当然有着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但他们在谈到郭沫若时表现出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他们对郭沫若到处题字的“调侃”,却并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来解释。他们对郭沫若的态度其实表现的是一种人之常情:对那些敢于批判我们和与我们为敌者,我们会痛恨、憎恶,而那些处处顺着我们的人,我们又会鄙视、轻蔑。罗点点还写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这样看来,1949年后的郭沫若,既未赢得工农出身的将相发自内心的尊敬,也让广大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不尊敬,真有点左右不是人了。
沫若之吻及其他(4)
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晚年的重要著作《李白与杜甫》,书中扬李而抑杜。据李一氓说,郭沫若“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也是根据毛主席的一些说法加以发挥的。主席好象就说过,他高兴李白不高兴杜甫。”(见刘茂林、叶桂生等著《郭沫若新论》)。在该书的《李白的家室索隐》这一部分结尾,郭沫若写道:“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经去过采石矶,看到了古人所谓的燃犀渚或牛渚。长江边上的太白楼也焕然一新。我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以纪行,抄录在下边,作为本文的结束。
久幕燃犀渚,来上青莲楼。
日照长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罶,
正是鲥鱼时节,我欲泛中流。
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什么样的奇思妙想都可能在他的笔下出现。这回,他要邀请李白同泛中流,并且同诵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李白也曾陪伴君王,但若非及时地去廊庙而游江湖,也就只能写出许多“云想衣裳花想容”一类的颂圣诗或“颂妃诗”,那也就没有可与杜甫并称的李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李太白,能接受郭沫若兴致勃勃的邀请吗?
2002年6月11日深夜
“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皆起于此夜之会”(1)
——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尽管习惯于用所谓“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把《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经典”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即使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然的产物”,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从而蔡可以“三顾茅庐”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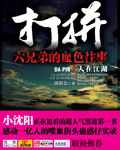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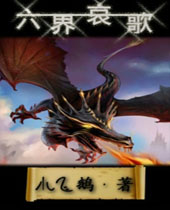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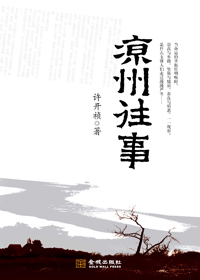
![[HP]霍格沃茨一段往事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18/188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