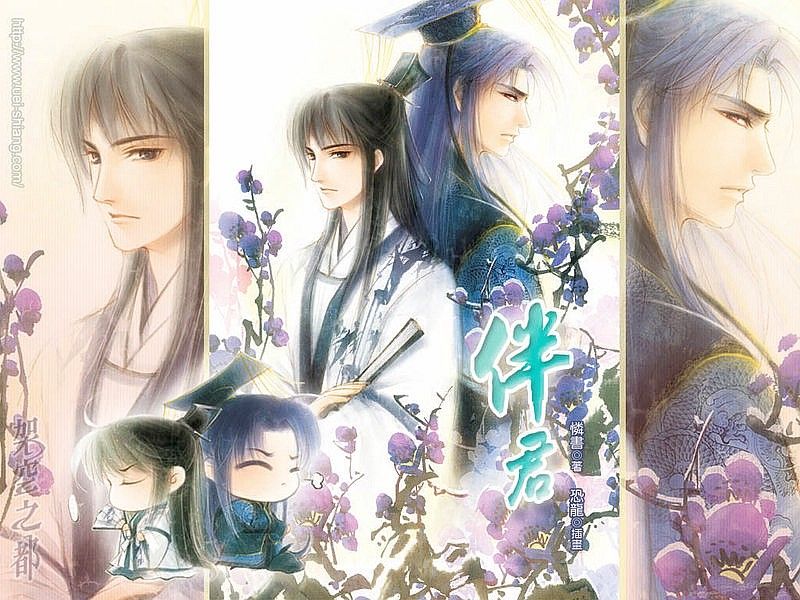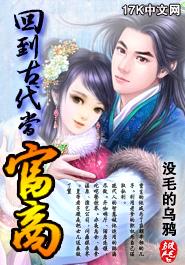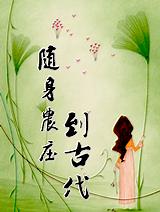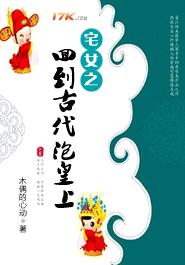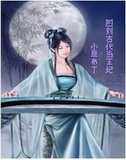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洗象工具
冈田玉山等人勾画出了“洗象”的工具。它们是:笛、校、橛、耳钩、筰、叉、、颈索。并加以注明:“笛”和“校”均为牛角制作,“笛”是吹发音令象进退的,“校”是缠象脚以制象乱动的。“橛”是立于河中缚象用的一大粗木。“耳钩”为铜制,长四寸余,因象耳广垂如荷叶,挂钩系之而洗。“筰”为洗象的竹刷,大约如董元恺《都门洗象词》所说的“双帚缚来洗刷”一般。“叉”长四寸五分,柄长三尺余,为铁制,是以叉口推象进退。“”九寸许,铁制,其状似滚筒。笔者理解,“”为
洗涤象身垢物、搔痒用的。“颈索”,是缚象头于橛用。雄象颈索三尺九寸,四十四曲,雌象三尺一寸,三十二曲。颈索上有径两寸的铜环。
冈田玉山等日本画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用什么样工具“洗象”,使如何“洗象”在人们眼前清晰起来,从而也填补了中国历史典籍中“洗象”的一个空白,因为在清代典籍中缺乏这种用工具“洗象”的具体记载。这正是许多中国的事物在日本赖以继承的一证。有道是“礼失而求诸野”,“汉文化圈”虽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个圈子里可以独尊,许多事源出于华夏,传入异邦,是异邦加以妥善的保存。应该说“汉文化圈”内这种交流,是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的,日本的文化根在中国,可日本人民通过交流,又加以变化,推陈出新,又反过来影响于中国,这从日本刀传入中国的史实中也可鲜明可见:
北宋的欧阳修,曾写过一首《日本刀歌》,但司马光也写过一首《和君倚日本刀歌》,笔者将这两首诗对照,发现除个别词句不同外,其余完全一致。他们在诗中均这样说道: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在他们之前,梅尧臣曾有一首《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诗中说道: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把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船帆落越栖湾汀。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坐中烛明魑魅遁,吕虔不见王祥老。
古者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
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朝廷重臣,见多识广,加之他们所处的时期科技昌明,可是他们却对日本刀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欧阳修、司马光所说:“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刀的质量上乘可以想见。
从历史典籍看,日本的冶金及制刀剑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的。可是日本却长期钻研,对制作刀剑加以变化,终于创造出了当时“汉文化圈”中最为精良的刀剑来。宋代的诗歌反映出了这一点。明清以来,这种交流的现象更为突出。据专家统计,明清时期日本输入中国的刀多达数十万把,《东西洋考》中就记录了当时的中国人多买日本刀,就是因为它“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
如嘉靖时,胡宗宪就曾得到一把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日本刀的制作水平是远远超过中国刀的。
正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日本刀甚锋利,“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由于日本刀具备这样好的质地,所以明代的兵器中比较重要的长刀、腰刀等,均仿日本刀制作,呈现出前代所无的新式刀制的模样。这种刀长其刃而短其杆,与旧式长杆短刃的长刀及大刀形制相反,其效能较大,可用猛刀砍劈,折断敌人长兵器的柄,或削断砍损敌人兵器的刃,进而砍断敌人的身体。
明代中国军刀运用日本刀之样式
这种仿造日本刀的做法,以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论述最有代表性:
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独用则无卫,惟鸟铳手贼远发铳,贼至近身,再无他器可以攻刺。如兼杀器,则铳重药子又多,势所不能。惟此刀轻而且长,可以兼用,以备临身弃铳用此,况有杀手当锋,故用长刀备之耳。
戚继光对日本刀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因此他所统率的部队也都装备了这种仿日本刀样式的长刀,在以短兵相接见长的“藤牌兵”的基本作战方式中,如“懒扎衣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等等,这种由日本刀变化而来的长刀,在与倭寇交锋时,发挥了所向披靡的威力。在优良的日本刀面前,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学习,而一旦中国掌握了这种器具又推广开来,又以中国样式、中国气派征服于“汉文化圈”,立于世界之林,这已成为“汉文化圈”中的一个规律,即人们常说的反馈与反反馈。
宋代真宗时期(998~1022),中国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引入耐旱的只需60天就能成熟的占城稻,浙江一带就以“占城早”、“六十日”而传扬,以至很长时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早熟水稻是受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影响,可史实上这种早熟稻的源头,是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传到越南的,又由越南再传回到中国。又如,中国宋代以前惟用团扇,元初时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都讥笑。从明代永乐年间始,日本送来他们学习中国制作的折扇,中国又加以仿效,很快全国通用这种扇子了。另外,中国虽以漆器制作长久而又精致著称,但却缺乏泥金画漆之法,明代宣德时期,中国特派漆工到日本,学到其法归来……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贡象”到“洗象”,从中国刀剑制作技术传入日本,又从日本传来其制作的“宝刀”,中国又加以变化、使用,“汉文化圈”这一系列的交流,都交织着中国与周边的越南、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它们已成为宝贵的、共同的财富,需要好好记取和发扬。
鬼市子
货殖撷趣 鬼市子(1) 作者:伊永文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用语,名称各异,但细细考察,都可从中窥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特殊之点,“鬼市子”便是一例。“鬼市子”出自《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同书同卷《东角楼街巷》条亦载: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
这两条史料告诉我们,所谓“鬼市子”,就是清早以衣服、古董为主要买卖的市场,附属于它的还有出售食物的小市。但为何市场冠之于鬼名?寓意是什么?《东京梦华录》则语焉不详。考之宋代典籍,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有一说明:
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汝适所言“西海”,为今日叙利亚等地,其货易方式自是阿拉伯民俗无疑。据此看来,“鬼市子”似乎还是舶来品,可明掌故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却作了这样一番考究:
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是鬼自为市也。《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又济渎庙神与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辄如数浮出,牛马百物皆可假借。赵州廉颇墓亦然,是鬼与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与鬼市也。谢肇淛的说法,不乏荒诞成份,说穿了,它不过是早市买卖的一种景象,之所以呼为“鬼”,首先与清早曦光微露,朦朦胧胧的氛围有关系。宋代《丁晋公谈录》云:徐铉在寒冬上早朝,看见待漏院前有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者,来往喧杂,此又为一证。而且这种买卖一到日出则散去,是有点鬼味。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则记:北宋治平年间,东京甘泉坊有一妇人,每天一大早就肩负着旧衣到市场上出售。一林文叔者,贫苦无衣,这位妇人便赠衣给他。两人日久生情,结为伉俪,后生一子,这位妇人化为鬼与林文叔诀别了……委心子说的这妇人,无疑是在“鬼市子”上卖旧衣,委心子又将她描绘为鬼,这大约是为了和“鬼市子”吻合或作一依据吧
魏泰《东轩笔录》记欧阳修曾说过——
在汉江野岸中,一天晚上,他听见歌笑语言,男女老幼特别多,其中就有交易评议,及叫卖果饵之声,好像市井似的,待天亮了才停止。第二天,欧阳修走上岸去,远望有一城基,一问才知是古代隋朝的城市。金代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又作“鬼市”说:阳武的裴择之翰林,六七岁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以大父马上抱往县东北庄,至外壕,见门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许,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来,市人买卖负担,驴驮车载,无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为妄,不之信也。盖三四至其处,亦皆见之。此与吕氏《碣石录》记“武平周鼎童时村居,一日,县人市集,鼎骑长耳,从父入市,时地色微,辨见道旁两列皆佛像,闭目不敢视,开目又不见”,两事大相类,但佛像之多何也
这类说法,显见是汉唐以来志怪小说的神韵,无非是为好事者和爱听“平话”等通俗文艺的百姓的消遣,是“鬼市子”的一种变异。最主要的是,作为限定买卖古董、衣服的“鬼市子”,由于商品特殊,自然而然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何况宋代商品的发达,已经为“鬼市子”制造了这样的机缘:
北宋开国之初,东京有一“何楼”,在“何楼”下面所出卖的物品都是假货。以后“何楼”因故废坏了,可是“何楼”之语却传下来了。其源就在于造假作伪不绝,可以达到有一真物,便有一假物,甚至时间一久,只知有伪者而不知有其真者。
就像史学家评价宋代这种假货市场所说:有以伪易真者,至以纸为衣,以铜铅为银,以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鬼”。在这样的大潮冲刷下,“鬼市子”的虚伪和欺诈自不待言。宋代陈纂《葆光录》所记的“俊鬼子”一事就是这样的典型:一军人早出,见一独足者卧桥栏上,军人少壮无惧,将此人抱起,那人是鬼,要求军人放他,可给予报酬。后来此鬼差人送给人一银盏。军人妻子认为不能用神灵物品,便让军人卖掉银盏,买酒肉祭祀。祭毕,军人向妻子说:其盏像家中银盏的模样,莫不是偷我们的吗?一看,果然如此……在清早出现的“俊鬼子”,赠军人的银盏是偷来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