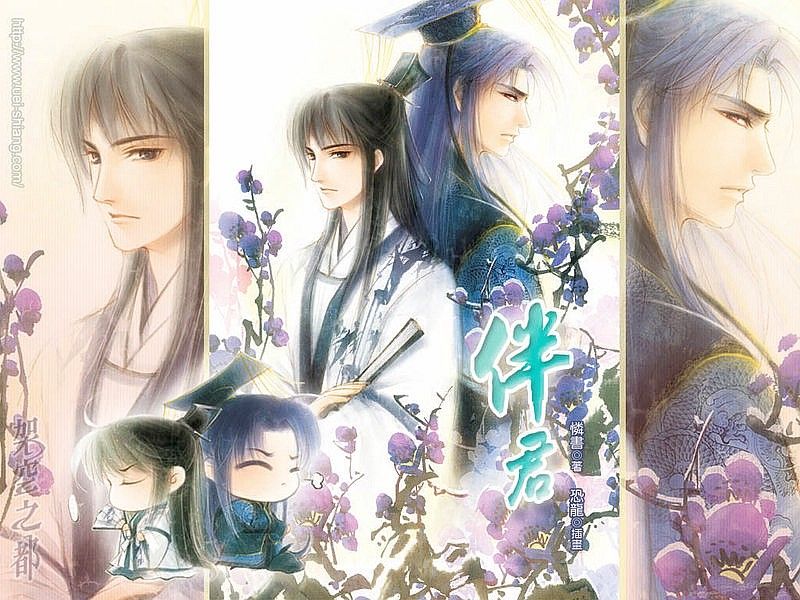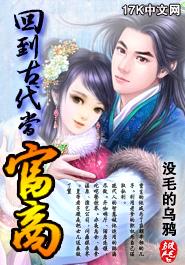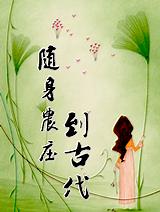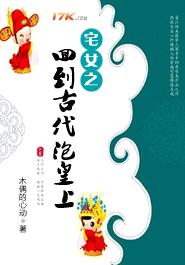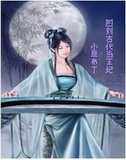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间则像秦淮河上燃放的“烟火”那样,“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盏、银台、赛月明、风车、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栏,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灭,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尤其年节,人们展开放“烟火”的竞赛,
明代有的县城要连放三日方休。在这方面,又以清统治者为甚。他们不惜将一笔又一笔巨资化为满天云彩。嘉庆十八年(1813),“造福海烟火法船一分,七夕、孟岁等项炮仗,以及山高水长烟火盒子,花炮并后湖小烟火二分,统计二十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件,按例需用银四千三十两二钱八分一厘八毫。并次年正月应用白日盒子一架、七尺千叶莲盒子一架、六尺盒子四架、花炮、起火等计二十万四千七十五件,照例需用银四千一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七厘一毫”。正是由于耗资巨大,一向以奢侈为能事的嘉庆在每次燃放“烟火”时也不得不考虑节省使用。
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则瞅准这一机会,投其所好,向皇家供奉许多江南制造的“烟火”精品,它们包括:七尺烟盒七架、喜庆灯帘七对、百果呈祥五架、四尺烟盒十架、三尺烟盒十架、尺六烟盒十架、七寸烟盒二十五架、金钱炮三十匣、小鞭炮二十匣、金丝菊二十匣、六合同春十匣、百福拱寿十匣、螽斯衍庆十匣、瓜瓞绵绵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芦十匣、流传万代十匣、刘海戏蟾十匣、金鳞集锦十匣、鸳鸯献瑞十匣、一统万年十匣、万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寿十匣、千秋万载十匣、仙果献瑞十匣、平安吉庆十匣、三报宫花二百五十个、金盆捞月二百五十个、头号起火五百枝、中号起火五百枝、大小花筒一千个、大小炮竹一万个。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8) 作者:伊永文
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可略见皇家燃放“烟火”靡费之一斑。皇家对“烟火”的热衷,使“烟火业”分外发达起来。明代王恭厂火药局一次爆炸,击坏西城三条街,伤百余人,从西直门楼上望去,周围三四里一带不剩一片瓦。这反映了明代“烟火”制造规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烟花爆竹的作坊竟达二十余家,赫然与其他日常消费作业并列。甚至小县城的“烟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没有的品种来,“如缸花、盒子灯、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灯、花炮、飞鼠、烟龙,不下十余种”,足见“烟火”制造普及之广。
“烟火”本来可以与军事火器的研制紧紧相连的。戚继光所统率的部队中,每一营都要部署一名“火药线匠”,这已经是将“烟火”运用于作战。可是“烟火”发展的路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向娱乐方面倾斜。南明弘光年间,马士英曾向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金的“烟火”,点放之际,“烟药中机造飞龙”,围绕殿柱腾跃,福王见状大加褒奖,于是,诸阁臣又共进了一架。这“飞龙烟火”,已属“火箭起火之制”。然而,“烟火”并没有被深入开掘研制,致使中国的军事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明万历时浙江的戴某,好与西洋人争胜,曾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铳中,第二机随之并动,不激火出而铳发,可射28弹。戴某本拟献于军营,可是他却夜梦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要遭报应!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这一念头。这一史料相当逼真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所笼罩的,宁可因循守旧于娱乐,也不愿意冒风险将“烟火”原理发挥、运用于新的发明创造上的文化氛围。
清代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提出用“烟火”制作技术造攻战武器的建议,并付诸于实践。光绪年间九江就有一“烟火”匠向省官献上一种能施放五里之遥的火箭,可是仅因为试验时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就使这位官员得出了“其言失实”的印象。这说明积极进步的创意是很难冲破由长期稳定的以皇权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识的。官宦想的是如何在“烟火”的娱乐性上下功夫,以媚上而“进身博官”;而皇帝只会对向他们频频燃放的“烟火”所表示出来的殷厚敬意大喜不止,很少念及如何将“烟火”向军事火器转化。
民间放“烟火”较为普遍的作用是祭神。清代《点石斋画报》对此有着传神的描绘。由于放“烟火”祭神造成祸害也是屡见不鲜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津草厂庵举办“烟火”祭神,“烟火”悬南马道,其药线蜿蜒数十丈。“大士像”的泥手插有香枝,枝端燃着,会头以药线一端,恭献“大士像”前,就火点燃,就好像是神仙点燃“烟火”似的,瞬息之间出庵,急行锐进,既达南马道。观者争睹,可忘了立足之地也是“烟火架子”陈列之处,正好在水中央,道的左右,均为秋潦,道宽仅可行一人,像独木桥。因“大士像”亲放“烟火”,为空前举动,小家碧玉,贫户妇女,纷纷赴水滨瞻仰,结果人一挤,纤足女流自然要遭到践踏的厄运,死状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在西方,拉瓦锡使化学系统化了;用于气体的收集和爆炸、燃烧和煅烧的实验、水的合成等各种用途的重要装置先后发明出来了;确证了质量在化学变化中守恒;化学的命名法作了改进,并逐步标准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第一流化学家,还引入了新的织物漂染的方法。
烟火略谈
宦海风云 烟火略谈(9) 作者:伊永文
这个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在化学工业方面已开始大规模生产硫酸和碱。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镇上,“烟火”的燃放,已达到了神出鬼没的境地:
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梨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
“烟火”技术角度上看,这种“烟火戏”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高的,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它已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景象,可是骨子里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然而它却仍以“今以手工,尊独惟我”,洋洋自得地表白。这就较为典型地折射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只看到海外一些表面现象但不深入吸收,以老大天朝自居的传统文化心态。
《点石斋画报·烟火奇观》,图中坐姿官员为李鸿章当西方接受了中国传入的火药后,马上制成火器,开辟出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用它打通了外部世界,以至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方以智也将火药当成从外国传来之物。清代则更是一塌糊涂。英国人在上海汇丰银行招待李鸿章时,为他燃放了一种忽海市蜃楼,忽孔雀展翅,忽成大庙的变幻多端的“烟火”,竟引得李鸿章大加赞赏,说“见所未见,可谓眼福不浅”。由中国人发明的“烟火”,都在英国人手中放出了异彩,从而引得中国最高官僚的赞赏,这真是辛辣的讽刺。但它却是史实,反映清代的落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此刻的西方,一本又一本的科学理论著作,排着长队来到世间,争相用科学的语言构筑起新的历史时期的基石,新型的化学工业大厦,已经在西方破土动工……可是,在中国,惟有赵学敏的《火戏略》,形单影只地步入技术科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步履悠闲地在宋元铺就的传统“烟火”园圃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惮烦难反复制作着昔日的辉煌,并转化出一些新的花样来,若“砉若雌霓起,霍若闪电惊”。看去“千花万花生”的“铁花烟火”,就是“冶铁既流,以大铁瓢挹而洒之著树间。辄迸火成花,灼烁夺目,此烟火又一变也”。保守的氛围,使人们不对“烟火”作任何非分变革的构想,尤其是明清统治者几乎听不到也不愿听到日益迫近的西方军团那似拍岸惊涛般的攻占新科学技术前沿的马蹄声……
从“烟火”进而发展制造火箭、飞弹,甚至喷气式飞行器等先进火器的优秀人才是有的,从宋元以来就积累起来的这种“烟火”实践是很丰富的,也是远远领先于整个世界的,可是明清的中国却没有把握住这一良好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正视欧洲科学技术挑战的机缘。直到先进的西方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轰穿紧紧封闭的古老城门时,中国这才如梦方醒,但为时晚矣。本来可以由制作“烟火”发展成为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火器的国家,却在清代彻底走向衰败的深渊,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沉思的。
小说中的“般载”与船舰
宦海风云 小说中的“般载”与船舰(1) 作者:伊永文
北宋时代陆地运输、交通工具,统称为“般载”。界画大师张择端,以其毫发毕现的画笔,在《清明上河图》中再现了“般载”的逼真形状:
画卷端首,五头小毛驴,背上驮两搭木炭,行进在树木夹峙的郊野小路上。在汴河虹桥上下,也有五头小毛驴,它们背上驮的是圆滚滚的粮袋子。在第一个十字街道上,在大街小桥边的大树底下,各有三匹“方匾竹两搭背上”的毛驴。在“孙家正店”前的一棵树下,有人正从两匹毛驴背上卸货。这些驮着粮食或货物的毛驴唤作“驮子”。如洪迈《夷坚志·夏二娘》所记,东京南薰门每早都有骡驮麦子联翩而来。在虹桥上,有一独轮车驰下。与之相呼应的是画卷另一端的护城河平桥上,也有一辆独轮车,同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一头小毛驴在前奋力拉着。这种车正是《东京梦华录》中的“前后两人把驾”、“前有驴拽”的“串车”。这是小串车,往往作“卖糕及麋之类”用。也有大串车,在悬挂着“新酒”幌子的“脚店”前停着一辆卸了货的大独轮车。在离汴河岸畔不远的一家小食店前,也停着一辆独轮车,一个店主模样的人站在支在车轮前的小梯上,看车上的货物。显然,这样的大串车,也可以“搬载竹木瓦石”的。也有人用这种串车推运轻软货物,如在写有“刘家上色沉”字样的商店前,也有一辆这样的串车经过。在迎面一爿“锦帛”铺前,也有一人站在一辆较小一点的空串车后面。可以断定,这种串车是用于一般的小商店拖运货物的。在第一个十字路口道上,走来一辆两头肥牛拉的带有棕盖的大车。《东京梦华录》对这种车作过详细描述:“两轮前出长木作辕。……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此车唤作“平头车”,又作“宅眷车”。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刘斧《青琐高议》别集说:一丧妻书生有一日出东京宋门,见一轻车驾花牛行于道中,车上有一妇人叫他。这些表明这类牛车主要是供妇女乘坐的。在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房脊后显露出来的牛车的一个侧面亦表明了这一点。只见它:棕毛盖厚重,车上有描画精致类似娱乐场所的那种门、栏杆和垂帘。这与《东京梦华录·皇后出乘舆》可互相参照:
命妇王官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担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