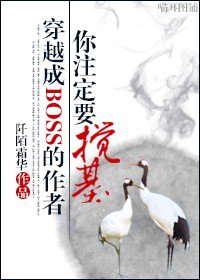坏坯子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必了,我开自己的车去。”勒恩说完转身便走。
勒恩并不是警局的主将,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连小兵都算不上。有些人觉得他很干练,也有人认为他表现平平。可是尽管如此,经过多年辛勤的工作后,勒恩毕竟也成了制暴组的成员。用小报的说法,这算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了。他一脸温良谦让,有个红红的酒糟鼻子,正值壮年,因久坐办公桌有点儿发福——就凭这副德行,众人也不会有别的想法。
勒恩开了四分钟又十二秒,来到指定地点。
萨巴斯贝里医院盘踞在一大片长方形的坡地上,主要大楼北邻瓦萨公园,东侧沿着达拉街、西侧顺着索尔街而建,大楼的底部被感化院湾伸展过来的新桥截断了。一间煤气工厂的红砖大楼从索尔街的蔓延过来,在角落边占据了一块地方。
医院的名称取自旅馆老板瓦伦特·萨巴斯。十八世纪初,萨巴斯在旧城拥有罗斯托克和雄狮两家旅馆,他在这儿买了地,还在池子里养鳄鱼,后来池子干涸或被填掉之后,萨巴斯在这里开了家餐厅,一七二零年他辞世前,总共经营了三年。
萨巴斯去世十年后,地上挖出了矿泉水,两百年的矿泉旅馆后来慢慢就变成医院和救济院了,如今这栋建筑则蹲踞在一栋八层楼高的养老院阴影处。
原来的医院是一百多年前盖在达拉街侧边的石地上的,包括许多由覆顶通道相连而成的棚子,有些旧棚子如今还在使用,很多最近才拆掉换新,原有的通道系统现在也已转到地下了。
园区尽头有许多作为养老院的旧大楼,还有座小教堂,花园的草坪树篱及碎石道问有栋避暑别墅。别墅漆着白边,圆圆的屋顶上有个尖儿,前面一大排树从教堂延伸到路边的旧警卫室。教堂后面地势较高,不过到了索尔街上面便不再爬升,地面在悬岩和对面的波尼亚大楼之间弯行。这里是院区中最安静、人迹最少的地方。医院的主要入口设在有百年历史的达拉街上,这是一百年前盖的,新的中央大楼就设在入口旁边。
第五章
巡逻车顶的蓝灯闪映在勒恩身上,让他觉得自己跟鬼一样。只是他没想到待会儿情况会更糟。
“发生什么事了? ”他问。
“还不清楚。总之很恐怖。”
这位巡警看起来非常年轻,他语气自然,怀着同情,眼神却充满了困惑,而且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左手扶着车门,右手慌张地抚着枪柄,勒恩十秒钟前刚到时,还听到他松了一大口气。
勒恩心想,这孩子在害怕呢。勒恩安慰他说:“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尸体呢? ”
“那地方不好找,你跟我的车去吧。”
勒恩点点头返回车里,尾随蓝色的闪灯绕过中央大楼,在院区里弯行。巡逻车在三十秒内向右转了三次,向左转了两次,然后在一栋黄墙黑顶的矮长建筑前停住。这栋大楼看起来非常古老,破旧的木门上有盏明灭不定的灯,灯泡外罩着老式的乳白色玻璃球,在黑夜中几乎起不了作用。巡警爬下车,站姿跟先前一样——手扶车门和枪柄,好像这样可以抵挡黑夜及待会儿要看到的事似的。
“在那儿。”他说,同时戒备而恐惧地看着双层木门。
勒恩按捺住呵欠,点点头。
“要不要我去找更多人来? ”巡警问。
“再看看吧。”勒恩好脾气地重复道。
这时他已经走上台阶推开右侧门了,门吱吱呀呀地响,因为门链久未上油。他又上了几级台阶,看到另一道门,门后是灯火暗淡的走廊。宽长的走廊天花板极高,贯穿了整栋大楼。
走廊一侧是私人房间和病房,另一边显然是准备作洗手间、寝具柜及检查室用的。墙上有部黑色的老式付费电话,打一次只要十欧尔(瑞典货币,一克朗等于一百欧尔)。勒恩盯着一个椭圆形的珐琅白盘,盘子上简单地写了两个字“艾玛”,然后他转头看着前面四个人。
其中两名是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矮壮结实,两腿又开站着,手垂身侧,两眼直视前方,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黑皮笔记本。他的同事低头靠在墙上,看着铁架上的珐琅洗脸盆,洗脸盆上有个老式的黄铜水龙头,勒恩在九小时的加班过程中所遇到的年轻人,大概就属这个年纪最小了。他虽然穿戴了货真价实的警察皮夹克、肩带,而且还配着武器,可是看起来却像个冒牌货。一名戴眼镜的灰发妇人瘫在藤椅上,眼光呆滞地望着脚上的白色木底鞋。她穿着白护士服,苍白的小腿上布满丑陋的静脉瘤。第四位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此人一头黑色卷发,正紧张地咬着指关节,他也穿了白外套和木底鞋。
走廊上的气味很难闻,飘着消毒水、呕吐物,或者是药品的味道。也许三者都有。勒恩突如其来地打了个喷嚏,他想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但迟了一步。
唯一对喷嚏声有反应的人是拿着笔记本的警员。他没说什么,只是指着一道淡黄色的门,还有打好字放在金属框里的白卡片。门没全关,勒恩轻轻将门拨开,里面还有一扇门也是半开着,不过这道门是往里开的。
勒恩用脚将门推开,向屋里望去,随即吃了一凉,他松开鼻子,又看了一次,这回看得更仔细了。
“我的妈呀。”他自言自语说。
勒恩往前踏了一步,让外层的门弹回原处,然后戴上眼镜,开始检查金属框里的名片。
“老天爷。”他说。
警员已收起黑色笔记本,拿出警徽,像念珠一样捏在手里。
好笑的是,勒恩想到警徽不久后就要被取消了。长久以来众人争执不休的话题——警徽应挂在胸口以直接表明身份,还是藏在口袋里——将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以后警徽会被普通的识别证所替代,警察只要穿上制服就成了。
“你叫什么? ”勒恩朗声问道。
“安德松。”
“你什么时候到的? ”
警员看看表。
“两点十六分,也就是九分钟前,我们刚好在附近的欧丁广场。”
勒恩摘下眼镜,看了一眼穿制服的男孩儿,这个小鬼脸色青绿,彻底失控地对着脸盆狂吐。年长的巡警顺着勒恩的视线看过去。
“他只是个警校学生。”他低声下气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巡。”
“最好去帮他一下。”勒恩说,“还有,去请第五分局加派五六个人过来。”
“请第五分局紧急出动,是,长官。”安德松说,差点儿没行举手礼或立正站好。
“等一下,”勒恩说,“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事? ”
也许他表达得不是很好,警员听了之后一脸困惑地瞪着病房门口。
“嗯,呃……”他支支吾吾地说。
“你知道里面那个人是谁吗? ”
“是尼曼组长吧? ”
“没错。”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呢。”
“是啊,”勒恩说,“差点儿看不出来。”
安德松离开了。
勒恩拭着额上的汗,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想了十秒钟,然后走到公共电话旁,拨了马丁’贝克家的电话。
“喂,我是勒恩,我在萨巴斯贝里,能过来吗? ”
“好。”马丁·贝克说。
“快点儿。”
“好。”
勒恩挂上听筒,走回其他人身边等着。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警校生,男孩儿不好意思地擦擦嘴。
“对不起。”他说。
“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
“我真的忍不住。这种事常发生吗? ”
“不会。”勒恩说,“我当了二十一年警察,老实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说完他转身对卷发男子说:“这里有精神病房吗? ”
“Nix verstehen 。”医生说。
勒恩戴上眼镜,看着医生白外套上的塑料名悼。
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乌兹库科科图普兹医师。
“噢。”他对自己说。
然后摘掉眼镜,静静等待。
第六章
那房间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高度近十二英尺,颜色十分单调——天花板呈污白色,而灰泥墙则似灰非黄。地上铺着灰白色大理石砖,窗框和门都是淡灰色。窗前挂着厚重的浅黄绸缎帘子,后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绵帘。白色的铁架床上是同色的床单和枕套,旁边有灰色的床头柜和浅棕色的木椅。家具上的漆都掉了,粗糙的墙面斑斑剥剥,天花板上的灰泥也多有剥落,有几处透着淡褐色的水渍。所有东西都很旧,却十分干净。桌上有个镍银制的花瓶,里头插了七朵淡红色玫瑰,外加两个玻璃杯、一只玻璃花瓶、一个里边放了两颗小药丸的透明广口瓶、一个小型的白色晶体管收音机、一颗吃了一半的苹果,以及一个装着淡黄液体的大玻璃瓶。下边架子上放了一沓杂志、四封信、一本线格纸、一枝有四种颜色墨水管的华特曼钢笔和一些散落的零钱——详细说,是八枚十欧尔、两枚二十五欧尔,以及六个一克朗的钱币。桌上有两个抽屉,上层放着三条用过的手帕、一块塑料盒装肥皂、牙膏、牙刷、一小瓶刮胡液、止咳片,以及一个放指甲剪、锉刀和剪刀的皮盒子。另一个抽屉里有皮夹、电动刮胡刀、一小包邮票、两只烟斗、烟草袋和一张印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空白明信片。椅背上挂了几件衣服——一件灰色棉外套、相同质地和颜色的长裤和一件长及膝盖的白衬衫。椅座上放着内衣裤和袜子,床边有双拖鞋。
一件米色浴袍挂在门边的衣钩上。
房里只有一种颜色显得格外突兀——那片触目惊心的猩红。
死者侧躺在床与窗户之间,由于咽喉伤口极深,头部几乎呈九十度角向后仰。他左脸颊贴着地板,舌头从张大的嘴中伸出,破裂的双唇间斜伸出断掉的假牙。
死者往后仰时,大量鲜血从颈动脉中喷出,溅得床单上片片殷红,洒得床头柜上的花瓶血斑点点。
死者腹部的伤口将他的衬衫整个染湿,在尸体边汇聚成一大摊血泊。从伤口判断,应是有人一刀捅穿死者的肝胆脾胃和胰脏,大动脉也被刺穿了。
死者的血可以说是在几秒钟内流光的,他的皮肤青白得近乎透明,额头、胫骨和脚掌部分儿乎可以看透。
尸骸上那道十英寸长的切口大剌剌地张着,刺破的脏器从腹膜边挤压而出。
这人几乎被砍成两半。
即使勒恩这种经常与血腥暴力为伍的人,对眼前这种惊悚的画面还是难以消受。
不过马丁·贝克从踏进房门那一刻起,表情从头到尾就没变过。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就像跟女儿去餐馆吃喝、更衣、做帆船模型、就寝前看点儿书,然后突然十万火急地赶去帮人查案一样。最糟的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马丁·贝克绝不容许自己畏缩,他天不怕地不怕,却害怕自己的冷漠。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十分了,马丁·贝克在床边席地而坐,冷静地仔细检查尸体。
“没错,是尼曼。”他说。
“是啊,我猜也是。”
勒恩站起来在桌上的物件堆中东摸摸,西看看。他突然打个大呵欠,然后不好意思地遮住嘴。
马丁·贝克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时间表之类的记录吗? ”
“有。”勒恩说。
他拿出一小本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