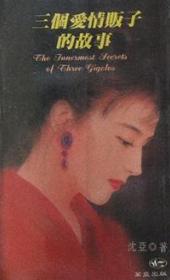奥利弗的故事 [美]埃里奇.西格尔-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是吓唬人,”坦普尔说。
“不是吓唬你。不过咱们这档子事你要是想快一点解决的话,也另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你这个妖精?”
他特意把那隐隐隆起的肌肉使劲抖了两下。我暗暗感到背后那帮音乐大师都为我捏着把汗。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有那么点儿。不过我还是不动声色地脱下了外套,把嗓门压得低了八度,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说道:
“坦普尔先生,如果你真要不肯自便,那我也没法子,我只能悠着点儿──读书人对读书人总得悠着点儿──来把你的橡皮泥脑袋揍个大开花了。”
那个吵上门来的家伙仓皇溜走以后,斯坦因先生开了一瓶香槟庆贺(“这可是加利福尼亚来的直销真品哪”)。酒后大家一致提出要在熟悉的曲子中选响度最大的一支来演奏,结果就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演奏得可真是劲头十足。连我还来了一份呢:我管打炮(用的乐器是一只空垃圾筒)。
几小时后演奏就结束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
“下次再来啊,”斯坦因太太说。
“他肯定会来的,”斯坦因先生说。
“你凭什么说得那么肯定?”她问。
“他喜欢我们哪,”路易斯·斯坦国答道。
情况也就是这些了。
不用说得,送乔安娜回家自然是我的任务。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她却还是一定要我陪她坐五路公共汽车回去。这五路公共汽车是一直顺着河滨大道去的,到最后才蜿蜒折进五号街到终点。她今天值过班了,所以显得有点累。不过看她的情绪还是挺高的。
“哎呀,你刚才真是了不起,奥利弗,”她说着,就伸过手来按在我的手上。
我暗暗自问:这手让她按着是个什么感觉呢?
我却就是说不上有些什么感觉。
乔安娜还是兴奋不已。
“今后坦普尔就肯定不敢再露面了!”她说。
“哎,我跟你说了吧,乔──对付蛮横的家伙,跟他来硬的其实也没啥了不起,就是像我这么个脑袋瓜子不大好使的,也照样办得到。”
说着我用双手做了个手势,所以这手就从她的手里抽了出来。(是不是觉得松了一口气呢?)
“不过……”
她的话没有说下去。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总说自己不过是个没什么头脑的运动员,她也许听得心里有些嘀咕了吧。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值得她白费时间的。说真的,是她太好了。人也算得上挺漂亮。反正只要是个正常的男儿汉,感情并不反常,对她的印象总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她住在医院附近一幢大楼的四楼。大楼是没有电梯的,我把她一直送到她的房门口,这时我才觉得她怎么长得这样矮呢。因为她说起话来老是得仰起了脸,把眼睛直瞅着我。
我还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急促。那决不会是爬楼梯的缘故(记得吗,我有跑步锻炼的习惯)。我甚至还渐渐觉得,自己跟这位又聪明又温柔的女医生说话时,怎么竟会隐隐然有那么一丝恐慌之感。
也许她以为我对她的好感可不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Ⅰ呢。
也许她还以为……真要是这样,那可怎么好呢?
Ⅰ意思是超乎性爱的爱。
“奥利弗,”乔安娜说了,“我本想请你进去坐坐的。可我一大早六点就得赶去上班。”
“那我下次再来吧,”我说。我顿时感到肺里缺氧的现象一下子就改善了。
“那敢情好,奥利弗。”
她亲了亲我。面颊上那么轻轻一吻。(她们一家子都是喜欢来跟人亲亲的。)
“再见了,”她说。
“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我回了一句。
“今天晚上过得真是愉快。”
“我也有同感。”
然而我心里却是说不出的不痛快。
就在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得出了结论:我得去找一位精神病医生看一看了。
七
“咱们先把俄狄浦斯王啊这一套Ⅰ撇开不谈。”
Ⅰ“俄狄浦斯王啊这一套”指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与王后伊俄卡斯达之子。长大后,无意中杀死了亲父。后因除去怪物斯芬克斯,被底比斯人拥为新王。在两不相知的情况下,又婚娶其母。发觉后,其母自缢,俄狄浦斯自刺双目,流浪而死。俄狄浦斯情结即指儿子亲母仇父的变态心理,这里显然是指仇父这一点而言。
见了医生,我精心准备的那一番自述就是这样开头的。要找一位可靠的精神病医生,有一套手续是少不了的,说来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首先得打电话找你做医生的朋友,说自己有个朋友需要找位精神病专家看看。于是你的医生朋友就介绍一位专家医生,让病家去看。
最后,你在电话机旁打了一两百个转,犹豫再三,才终于拨通了电话,约定了去诊所初诊的时间。
“不瞒你说,”我就一路往下说,“这种课程我也学过,咱们这话一谈起来,用那套行话术语该是怎么个说法我都清楚。跟詹尼结婚的时候我对待父亲的那种态度该标上个什么名称我也了解。总之,按照弗洛伊德那套理论的分析,并不是我今天来向你请教的目的。”
这位埃德温·伦敦医生尽管据介绍人说是个“极风雅”的人士,却是不大喜欢多说话的。
“那你来干什么呢?”他毫无表情地问。
他这话倒叫我吃了一惊。我的开场白已经顺利说完,可是还没有容得我歇一口气,“反诘问”就已经开始。
说真的,我到底想来干什么呢?我到底想要听他说些什么呢?我咽了口唾沫,回答的声音轻得几乎连我自己也听不见。
“我弄不懂自己怎么会变得没有感觉了。”
他没有作声,等着我说下去。
“自从詹尼死了以后,我简直成了个无知无党的人了。当然,有时肚子也会觉得饿。那只消快餐一客就能对付。可是除开了这一条……这十八个月来……我可以说完全成了个无知无觉的人。”
他就听着我说,由着我苦苦地把心里的想法统统挖出来。种种念头乱腾腾一齐往外涌,带来无尽的伤痛。我感到难受极了。不,应该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那只有更难受。自从没有了詹尼,我就像把魂给掉了。幸亏有菲利普。不,其实菲利普也帮不了我多大的忙。尽管他也确实尽了力。我就是什么感觉也没有。差不多有整整两年了。我跟正常人相处就是激不起一点感情的反应。
话说完了。我身上直冒汗。
“感到有性的要求吗?”医生问。
“没有,”我说。为了讲得再明确些,我又补了一句:“一丝一毫也没有。”
对方没有马上接口。是医生感到吃惊了?从他的脸上我可看不出一点表情。我想反正这是彼此都一目了然的事,所以就又说道: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是心里负疚的缘故。”
这时埃德温·伦敦医生开口说了他那天讲得最长的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你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呢?”
我是不是觉得我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我立刻想起詹尼去世的那天我曾情不自禁起过一死了之的念头。不过那只是一闪念。
我懂得妻子得白血病,那不是丈夫造成的。可是……
“可能有一点吧。我好像一度有过这样的想头。不过我主要还是生我自己的气。有很多事情我就是没有能趁她在世的时候替她办到。”
沉默了一会儿,伦敦医生才说道:“举个例子看呢?”
我又谈起了我跟家庭的决裂。说因为詹尼的出身地位跟我稍有差异(其实差异可大着呢!),我就借跟她结婚一事,来向世人宣告我脱离家庭而独立了。看吧,腰缠万贯的老爸,你看我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
只有一件事我失败了。我弄得詹尼很不痛快。不只是在感情上。
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我就已经弄得她够苦恼了,因为她敬爱父母的那种感情之深那真是没说的。可是更使她苦恼的,是我坚决不肯再拿父母一个子儿。在我这是大可引以自豪的事。可是,唉!詹尼是从小生长在穷苦人家的,要是到头来还是落得一点银行存款都没有,对她来说这种日子跟以前又有什么不同可言?又有什么优越可言?
“就为了迁就我这口傲气,她不得不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
“依你看她也认为这是她作出了牺牲?”医生问道。大概他根据直觉认定詹尼始终没有出过一句怨言。
“大夫,今天再去揣测她当时是怎么个想法,已经没有意思了。”
他对我看看。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真怕自己要……要哭出来了。
“詹尼已经死了,可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多么自私。”
歇了半晌。
“怎么呢?”
“那是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詹尼申请到了那么一笔奖学金,本来可以到法国去继续深造。可是到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她却二话没说。两个人就是一个心眼儿:结了婚就留在坎布里奇,让我进法学院读研究生。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又是一阵沉默。伦敦医生没有开口。所以我就又继续叨叨下去。
“我们觉得不这样办就行不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我这口要命的傲气!就是为了要表明我的事业生涯比她的重要!”
“可能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伦敦医生说。他是想减轻我的内疚,不过这种手法不见得高明。
“反正我了解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呢!我难道就不能先陪她到法国去,宁可迟一年再来当我的律师?”
大概他以为我是看了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资料,事后想起才感到不胜负疚的。他完全想错了。我所以这样痛心,倒不是因为我阻碍了詹尼的“进一步深造”,而是因为我没有能让她赏赏巴黎的风光,一睹伦敦的胜迹,领略领略意大利的情调。
“你明白啦?”我问他。
又出现了冷场。
“你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他问。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明天五点再谈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他也把头点点。我于是就走了。
为了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我就顺着公园大道一路走去。一方面也好准备准备,迎接这底下的一步。明天就要开始动手术了。在心灵上开刀,我知道那不能不疼。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收效如何。
八
一连去谈了个把星期,这才接触到了俄狄浦斯那一套。
哈佛园里的宏伟大楼巴雷特堂,是谁家造的?
“是我们家祖上出资造的,为的是要买个好名声。”
“为什么呢?”伦敦医生问道。
“因为我们家赚的钱不干不净。因为当年我们家的祖上率先办起了血汗工厂。别看我们家好像很热心慈善事业,那只是近年来才学会的消遣。”
说来奇怪,这段历史我倒不是在写巴雷特家族史的什么书上看来的,而是在……在哈佛听说的。
那是我念本科四年级的那年,我因为学分不够,得想法捞几个容易到手的学分来充充数。所以除了其他许多课程以外,我还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