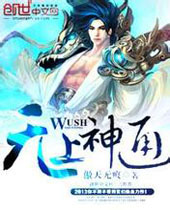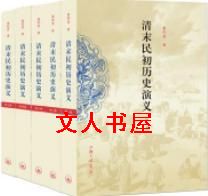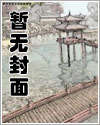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神秘的谶言 作者:世外老人-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权时; 才改名建业。 在把东南许多地方的天子气都折腾一通后,秦始皇于公元210 年,始皇37年,死在南巡的路上。
东南经秦始皇么一折腾,其它地方,还有多少天子气,不得而知,但金陵的天子气,象是属免子的。如果说金陵没有天子气,金陵在历史屡次作了一些王国的国都; 号称六朝故都。中国历史上,吴,东晋、刘、宋、梁、陈,之后还作过南唐,南宋,明,太平天国,还有民国,都建都金陵。 可几乎所有建都金陵的王朝,要么是做不长,要么是做不大。唐朝诗人刘禹锡曾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说,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刘禹锡只是说了三国时期吴国“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事儿,其它建都金陵的王朝,都碰到过“一片降幡出石头”的事件。金陵王气是不是真的黯然收了。和秦始皇有没有关系?也只有天晓得!
在秦始皇到金陵之后,他身边有善望气者说: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
还有说法是:五百年后,金陵为天子都。这话记载于《晋书,元帝纪》中。
公元222 年,吴王孙权称帝时,他认自已就是应了这句谶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所以宣布即皇帝位。当然不是句话谶言,促使孙权做成了皇帝,按《建康实录》里的说法,是这句谶言促使孙权做皇帝决心。谶言,在孙权称帝的时,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但吴王孙权称帝时,为公元222 年。秦始皇手下善望气的术士说说谶言的时间,大约在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前后430 年时间。时间上不足500 年。
而且孙权创建的吴国,占据中国东南一偶,国土面积不足中国三分之一; 到他孙子投降时; 人口才两百余万; 不足当时中国人口四分之一。 所以孙权创建的吴国,不足以代表中国。
有人认为,秦始皇时术气所说的“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不是应在孙权的吴国,而是应在公元317 年司马睿所创建的东晋王朝。
其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较为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匈奴、鲜卑、羌等各族,统称胡人。大多的汉族成员,到了南方,所以公元317 年由司马睿创建的东晋王朝,建都金陵,此时的金陵才够资格称国都。而从公元前210 年,到公元后317 年,520余年时,与谶言里的五百年后,可以应验。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看,金陵的天子气,是免子的尾巴—长不了。但东南的天子气却相当旺盛。
东南对于中国许多人来说,不是一个地理名字,而是一政治名字,它是以秦王朝的国都咸阳为座标,在咸阳的东南方向。这片地域较为辽阔,如江苏,安徽,浙江省,福建等南方许多省分,都属中国之东南。
在这一地区,中国历史上百分之八十的开国皇帝,(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身于这一类地区。如取秦而代之的汉高祖刘邦,出生于江苏沛县,魏武帝曹操出身于安徽安徽亳州,朱元章也是出身于安徽凤阳。
这些东南的真命天子们,一个个地从东南冒出来。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而且中国的东南角天子气,还是相当旺,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天子气,从中国的东南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如果真有一个什么天意,愿让天子,或能做天子的人,从那儿冒出来,这些“天子”们只要上不违天意,下能得民心,我们凡人愿意乐见。
晋祚尽昌明
一、皇帝是“同志”。
晋咸安元年; 大司马恒温恃其材略威望; 有不臣之心。
相士杜炅,据说能识人之贵贱。恒温请来杜炅,给他自个儿相命。杜炅对恒温是左看、右看、上下看;看了恒温的面,再看恒温的背;看了恒温的侧面,再看恒温的正面。之后用略带有遗憾口吻,对恒温说:“大司马功高盖世,勋格宇宙,位极人臣!”
在恒温请杜炅来给自己相命时,恒温的不臣之心,在当时的东晋王朝,也是路人皆知。杜炅不是生活在东晋王朝的空气之中,他对于恒温请自己相命可能导致的政治事件,心里十分清楚。但他看了恒温面相之后,说恒温只能“位极人臣”。有两种可能,一,杜炅是想从心里是打击恒温的不臣之心,从而保护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另一种可能是,在杜炅看来,恒温真不是做帝王的料。
恒温听了杜炅的话,十分失望; 但没有心死,他对左右人说了一句十分著名的话:“男子汉如不能流芳百世,亦遗臭万年!”这话说得让当世及后世许多冒险分子提气。恒温是瞄准了东晋王朝皇帝的位置,非国家最高领导人大位,不足以动其心。
当时东晋王朝皇帝司马奕,为人低调内敛。《资治通鉴》说其人“行事素谨。”朝庭大事小事,要么是大司马恒温说了算,要么是丞相司马昱说了算。这位皇帝,在臣民心中,算是一个没头没面的皇帝,没有什么太崇高和德性,也没有十分特扎眼的绯闻、丑闻。大司马恒温想立马在皇帝身上,找出个什么茬儿,一时还不太容易。
所以恒温想要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来着,但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开始的借口。然后发动政变,或者号召群众。但皇帝就是没给恒温这个机会。这让恒温十分头痛。司马府里的狗头参军郗超通透恒温心思。他给恒温出了一阴毒的主意:说污蔑皇帝是“同志”。有同性恋倾向,对同性有兴趣,对异性无性趣。(《资治通鉴》“帝有痿疾”。)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又污蔑说,皇宫里的内待,相龙、朱灵宝等人,都是皇帝男宠。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这些男宠借服待皇帝之名,与皇帝现有的二位美人,田氏,孟氏乱搞。生出了三位皇子,其中一位会被立为东晋王朝太子!
郗超在获得恒温喑中支持之后,通过各种法子,四处散布皇帝的绯闻。一时间,健康的大街小巷,许多人都在谈论皇帝的绯闻事件。
所谓“床弟易诬”。历来皇帝的后宫生活,对于普通人来的说,本就神秘莫测。现在许多臣民听到当今皇帝,在后宫搞出这等丑事儿来。他们许多人义愤填膺起来,这可是国家第一丑闻。是可忍,熟不可?
两个月后,恒温看到朝臣民众,对于皇帝是同志这件事儿的关注度,近于沸点。他便从姑苏赶到健康。向皇太后建议,请皇太后下令废了皇帝!
二、皇太后致命的读后感。
此时东晋王朝的皇太后,不是当今皇帝司马奕的亲妈妈。她是东晋孝宗穆皇帝司马聃的老婆,与现任皇帝,没有任何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在皇宫里,皇帝没有把皇太后当做自个儿亲妈看;而皇太后也没有把皇帝,当做自个儿亲儿子看。现任皇帝仅名义上,作为晋孝穆宗的嗣皇帝,入继皇统。皇太后,是皇帝司马奕的挂名儿的娘。
皇帝对于这挂名的娘,不大放在心上,平日孝心尽得也不到位,所以皇太后对于皇帝,早就是有一肚子的不满意,正想找一个出口发泄!
大司马恒温偷偷地进入太后宫,向皇太后告皇帝的黑状。此时皇太后正在礼佛。接到大司马奏章,太后才看了奏章里的几行字,就对大司马恒温说:“我早就怀疑这件事儿了!”(《资治通鉴》:太后云,我本自疑此!)
大司马的弹劾皇帝是“同志”的奏章,皇太后都没有看完,只看了一半,就命左右取笔,在大司马恒温弹劾皇帝的奏章上,批了一行意见。确切地说,应是皇太后对于皇帝“同志”事件的读后感:“未亡人不幸,遭此百忧,感念存没,心如刀割!”
恒温拿到太后的读后感,如捧至宝,他的心里象是开了几千朵花儿一样。恒温诬皇帝是同志这件事儿,太后虽然没有直接下旨如何处理,但太后在他奏章上批示的读后感,是对这件事件的最高定性。
现在,皇帝是“同志”肯定,皇帝的“同志”淫乱皇宫肯定;太后的读后感,间接对于皇帝的糗事儿,进行了证明。
太后的肯定与证明,到了老狐狸恒温手里,就成了皇帝夺命的刀剑。皇帝司马奕的命运,就在大司马恒温与参军郗超最无耻、最卑鄙、最下流的阴谋之中,调谢了!
几天之后,大司马恒温以大司马的名义,招集朝臣,开东晋王朝的中央扩大会议。在京各部门、各衙门的重在首长;地方上的重要大员,都到朝堂参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迟到或缺席!会议的内容只有一个:皇帝无行,废帝另立!
若干若干年之后,司马光老先生回忆这个事件时,在他的著作里说:此议一出,百官震悚。在古代中国,大臣们的位置可以变来换去,大臣们的脑袋也可以被一些无良的皇帝、无赖的皇帝的砍来砍去。但没有多少人敢明目张胆地说要废了皇帝!
废皇帝的事儿,在恒温之前,只有汉王朝的霍光一个人干过。从霍光到东晋之世,也有五六百年时间了,还有人站出来,说要把皇帝给废了。对于东晋王朝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来说是,是不敢想,也是闻所未闻的。
一时间,王朝数千官员,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他们许多人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也有见风使舵快的大臣,想跟着应和大司马,但却不知如何应和!
皇帝可以废?
怎么废?
咱中国人,只要是想搬到桌面上说的事儿,都要讲一个礼仪,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恒温要搬到桌面上,让大伙讨论,是不是应有一个废帝礼式?
另外,废帝是象犯了罪的大臣一样,是不是应追究他的法律则任?
古人们都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皇帝犯罪,或者有过错,是不是也应与庶民同罪?
百官们连气都不敢吭出声来。皇帝听到待者宣读弹劾自己的奏章; 及皇太皇的读后感之后; 吓面无人色!
三、风流在晋朝。
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也是特别的王朝。许多史学家在提到晋朝里,都会提到一个令人心醉的名词:魏晋之风流。
魏人晋人之风流,包括几个层面的意思,有指魏晋之世,文化艺术之风流,后世中国文化人所喜好的琴棋书画,在魏晋之世,全面复兴;有指当世人物品性之风流,如风流倜傥的健安才子,如书艺冠绝天下的王羲之父子,或如嗜酒,好清议的竹林贤士们。
魏晋之世,特别是到了南方的东晋王朝,盛才文化与文化人,但文化人思想上的自由,却是以皇权的退却为基础!
其时,西晋王朝在中原战场上,吃了大败仗。皇室贵族们狼狈不堪地逃难逃到南方。南下稍安之后,对于朝臣,对于文化人的控制,要比以往及以后任何王朝都要松懈。甚至为了抵抗外敌,聚集民心士气,皇帝不惜下放皇帝的专有权力,与朝臣分享。所以才有了东晋开朝之初,“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朝臣们风流了,快活了,皇帝的日子自然就不大好过。很难想象,在明清之际,皇权高度集中情况下,中国人中,还有谁敢象魏人、晋人一样,自命风流?
同样,也不敢想象,明清之际,有那一个家族,敢对明朱皇帝,爱觉新罗氏的皇帝们说:我与你,共天下?
到东晋咸安元年,最初与司马家族开创东晋王朝的王氏家族没落了。换成了为司马家族做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