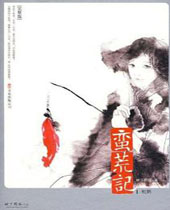读城记-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边,当然“立等可取”;而所谓“又靓又平”,则是“价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广州人偏偏不按国内通行的方式来说、来写,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结果,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堡、牛腩粉、云吞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火屈)”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诱导下点了“牛奶”,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里还再敢问津“獭尿虾”。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 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
当然是在中国,只不过有些特别罢
①士多,买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片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明信片。贴士,小费。晒士,尺寸。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话说:“千里同风不同俗”,广东却是连“风”也不同的。大庚、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便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衣食甚异,这就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蚌(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一。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图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
“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柏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爱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罐堡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它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
现在可就不一样 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坐失良机。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的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 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