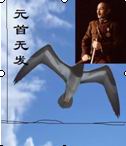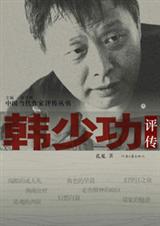严复评传-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12月20日,与王夫人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曾与严复交谊甚笃的晚清内阁学士陈宝琛为他撰写《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墓志铭》曰:“君子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有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皆行于世。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主要参考书目
主要参考书目
一、严复著译资料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八种。
马勇编:《严复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二、严复传记资料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收入《严复集》第5册。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收入《严复研究资料》一书。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入《严复集》第5册。
钱履周遗著,何佳春整理:《严复年表》,载《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76年版。
王栻、俞政:《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吴湘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7年6月版。
三、严复研究论著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版,台湾中华书局民国76年版。
(美国)许华茨著,滕复等译:《严复与西方》,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牛柳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王中江:《严复与福泽渝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高惠群、马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后记
后记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自己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栻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周先生离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栻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慈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刺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确认。
现在看来,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其中还包含一个历史观念的清理间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输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响到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反省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更多地是看到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应沿承历史的惯性,将其流弊加以放大。
学术不分国界,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学术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传统,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尚处在封闭、保守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与西方文化交流,强调认同世界文化的主潮,这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今天,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上来,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自身的学术——国学加以重新开掘和发展,从而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学术对话中的份量。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最后,我想对自己写作《严复评传》提供了帮助和指点的刘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来北大研究期间,刘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我的学术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责任编辑钱宏本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态度,在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却为中国学术操忧,走向国学这块寂寞的园地,这种负责任的编辑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参加丛书写作的同人感激。
欧阳哲生
1994年2月27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 … 。………【gzbysh】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