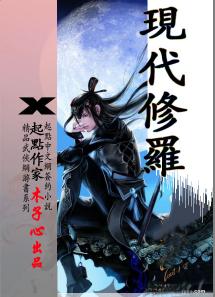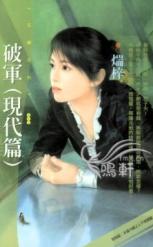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穑坎淮恚沂咀时局饕逯贫认碌慕鹎叵档闹魈猓 ≡诮难е校乇鹗桥邢质抵饕遄髌分惺遣环ζ淅模膊捎霉』嫉摹 ∈侄巍5饫嘞质抵饕宓摹 笆敌捶ā辈荒茉斐删嗬敫谢蚰吧校荒芰⒖獭 “讯琳叽胂蟮牧煊颍吧幕肪常蚨幢啬苁盏较蟆 侗湫渭恰纺恰 ⊙苛业囊帐跣ЧR蛭嗣敲娑砸桓觥 安∪恕保话愫苣讯先凰喝ツ俏虑椤 ÷雎龅拿嫔矗薇A舻芈冻鏊恼媸蹈星椋辽倌悴豢赡苡美闷还蓝樱 ∮媒挪人。ǜ盖祝豢赡芗柑臁巴绷烁头梗妹茫O衷诿娑缘氖恰 ∫恢患壮妫桓霾辉倌苡醚杂铩⒂帽砬槔幢泶锼那楦械摹 袄コ妗保憔臀蕖 ⌒胗萌魏涡榧俚淖颂囱诟悄谛牡难岫窳恕U饩褪怪魅斯沟椎卮印 叭恕钡摹 ∈澜绶掷氤隼矗闪艘桓鲇肴魏味锩挥斜局什畋鸬摹 胺侨恕薄S谑侨擞肴恕 ≈涞睦淠叵稻拖拭鳌⑶苛业亟沂玖顺隼础U庵止叵稻褪前髦贫仍斐傻摹ⅰ ∥薹ǘ糁沟娜擞肴酥涞摹 耙旎薄U庵帧耙旎笔瞧毡榇嬖诘模灾氯嗣恰 ∠耙晕#抟跃醪炝恕O衷诳ǚ蚩ㄍ蝗灰簧毂蓿砸桓鼍耸录讶粘! 〉拇嬖诩右哉鸲谷嗣堑南胂蠓扇胍恢帜Щ萌Γ缓笏匀粘5挠锲⑵健 【驳谋实鳎疤衣览础薄=餐炅耍Щ萌ξ扌蜗В凑馐俏颐侵堋 ∥У钠匠J虑椋皇俏匆鹱⒁舛选7研钥ǚ蚩ǖ恼庵直硐质址ㄗ鞴 『芎玫拿栊矗骸 部ǚ蚩ā惩ü恢钟靡员硐种鞴鄣目凸凼挛铮ü恢指耸隆 〖匀粘M夤鄣挠镅裕共黄骄驳氖虑榛挂黄骄玻鼓吧氖虑榛挂 ∧吧6遥员砻嫔吓怨鄣淖颂逊浅5氖虑樾吹煤廖尢乇鹬Γ ∏О偌械囊患谜庵址椒ú唤龈浅J挛镌斐刹豢杀饶獾木В ∏胰萌烁芯醯秸馐且患裆形淳醪臁⑾衷谝狄驯┞兜娜粘J虑椤D且弧 《缺焕寺捎弥溆锛で榛狡鸬墓砉帧切枰桓龌孟氲幕肪场弧 ∪恢渚驮谖颐堑敝校弧 罢P浴钡氖挛铮匆桓鲋魅斯兄霸薄⑼痢 〉夭饬吭被蛉魏我桓銎掌胀ㄍǖ娜恕牟灰俗⒁獾拇嬖诳蓟牖谩 ∠胧挛镏校欢獠⒉皇鞘裁幢鸬亩鳎潜浠诵翁摹⒋佣弧 〗铱说娜粘P缘亩鳌Bㄆ跸匀槐豢ǚ蚩ǖ恼庵止值苛业谋硐帧 ∈址ㄋ鄯担骸 】峙潞苌儆凶骷以谒堑淖髌分邪盐帐澜绾驮傧质澜绲氖焙颍馨选 ≡镜亩骱突镜亩鳎馨讯允澜缟洗游闯鱿止氖挛锏木欤蟆 ∷淖髌分心茄硐值萌绱饲苛摇T诮裉欤谀侵质笛樾缘幕蚯宦伞 〉募记烧莆兆哦嗍髡哂攵琳叩氖焙颍庵滞怀龅母鲂员囟ɑ岣肆粝隆 ∧淹挠∠蟆U蛭值缬玫们〉保苋〉谜庋恍┨厥獾囊帐跣Ч ∷运辉嚼丛蕉嗟娜怂邮埽⑶乙炎魑恢钟哪氖侄稳〉妹姥系囊狻、佟 ·费歇尔: 《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322 页,维也纳,1962 年版。 ② 卢卡契: 《批判现实主义的现实意义》533 页,1958 年版。
义,成为现代审美特征之一。桑塔耶那认为,以变形为基本特征的怪诞也是 一种“再创造”。“正如出色的机智是新的真理,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 因为它们 “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① 悖谬 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有时会令人感到如陷迷宫。但一旦你找到如希腊神 话中说的米诺塔鲁斯的线,被牵出迷津暗道时,你便会感到它回味无穷。这 里卡夫卡又把哲学引进了文学,运用了哲学上的一个逻辑范畴:悖谬 (Paradox,也叫背论、反论,这是形式逻辑的术语,类似“二律背反”,含 有悖理、荒谬、自相矛盾、似非而是等意思)。西方一些对卡夫卡发表过权 威性见解的作家、评论家都指出: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基本特征。在卡夫卡 之前,文学创作中即使有此先例,也不是常见的,但这一哲学——艺术手段 在当代第一流作家中是不鲜见的,如迪伦马特,他不仅提出了 “在悖谬之中 见真实”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中运用得十分出色,如他的代表作 《贵妇 还乡》、 《物理学家》、《罗马路斯大帝》等。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 也是运用悖谬的极好范例。可见悖谬是一种富有艺术效果的手段,它可以增 加戏剧矛盾的色彩,产生摇曳多姿的情趣和耐人寻味的魅力。 悖谬是在自相矛盾中构成的。它总是同一种正常轨道的脱离或倒转相联 系。为了便于理解,卡夫卡设计了一个鸟寻笼子的 “图像”,他把这个图像 改成 “笼子寻鸟”,就成了悖谬。但卡夫卡的悖谬不仅仅把正常的思维轨道 倒转就完了,他总让你的思维在逻辑的与反逻辑的轨道上来回滑动,可始终 不让它到达两个极的顶端。所以前西德学者格 ·诺伊曼称卡夫卡的悖谬为“滑 动悖谬”。这种手法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产生一种令人思索无穷的意味;它们 常常给人一种似非而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感觉。 最早发现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特征的恐怕要算加谬了,一九四二年他就 指出: “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 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 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他们以反响和意义。要想理 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① 现在来看一下他那些主要的小说吧。它们的中心事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 荒谬的,但荒谬仅是表面,思维沿着非逻辑的轨道滑动,未及到达顶端它又 倒转,滑上逻辑的轨道。城堡可见而不可及,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当 你把它作为反动官僚专制主义统治与人民严重对立的象征,或当你想到有时 想办一件事而又困难重重,从而发出 “比登天还难”的感慨时,你不觉得它 在艺术上比真实还真实吗?在卡夫卡自己所珍爱的短篇 《判决》中,主人公 因顶撞了一句父亲,即被父亲判处跳河自杀,儿子竟然毫不犹豫地服从了。 这显然也是离奇的。但再一想:既然这位父亲在家里占有这样的家长制的绝 对威权,而儿子又始终摆脱不了这位 “专制犹如暴君”的家长的巨掌,那么 这位父亲存在的本身不就是对儿子的致命威胁吗?反过来,儿子由于深感自 己无能,不能尽家庭义务,从而产生“无穷尽的负疚感”,那么跳河的“判 ① 桑塔耶那: 《美感》175——17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加谬: 《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载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1973 年版。
决”对他岂非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吗? 《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被无端逮捕, 他为洗清自己的清白不遗力地奋斗了多年,可最后被处决时,他竟又顺从地 引颈就刎,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若按照卡夫卡的思维特点,则也合乎逻辑: 在法庭面前约瑟夫·K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 不小的官员,他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也高高在上地对待过 那些在银行门前苦苦求告的百姓。因此他虽不接受国家法庭的判决,他却应 该受到 “自我法庭”或那超自然的正义法庭的判决。《饥饿艺术家》的主人 公在表演到期时已饿得奄奄一息,但他愤愤不平:为什么没让他继续饿下去? 这种自我折磨狂也令人费解。但这有什么奇怪呢?他既然是个 “艺术家”, 他当然应该有艺术的事业心;而他的艺术手段是 “饿”,那么他要达到艺术 上精益求精,或显示自己的艺术造诣,除了继续饿下去,还有什么其他途径 呢? 对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手法的艺术魅力和奥妙感受得最深切并表达得最 生动的恐怕要算捷克血统的美国学者埃利希·海勒,他说: “始终无法解释 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 又好象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势,而 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 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自传性 卡夫卡是一个内省的、思辩的、带玄学味的人,这一性格特征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即他把写作当作他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卡夫卡在 他的大量的日记和书信中,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 “双重生活”的矛盾,即 他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的冲突,或者说他的感觉世界与观念世界的争斗。 ① 他的外表笑容可掬,内心却“没有一秒钟的安宁”;白天,他是工伤保险公 司的一个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员,晚上,他的思想却在内心世界的无限空间自 由驰骋;在奥匈帝国那个窒人的环境里,他是个奉公守法的臣民,在他的专 制的父亲面前,他是个从不逃避家庭义务的孝子,但他的内心却激荡着不屈 服的叛逆情绪,是个 “本性好斗的人”(《内心日记》)。这种“可怕的双 重生活”使他感到 “被撕裂”的“痛苦”,他觉得“除了发疯,看起来没有 ② 别的出路”。 不过,卡夫卡到底没有疯,因为他感到,创作之于他是将“内 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的推进”的手段, “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而“是一种 ③ 奇妙的解脱和超凡的生活”。 因此他决心“要不顾一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 ④ 来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于是他的笔输导着他的被压抑情感 中痛苦的流液,他的书收获着他的观念世界中一个个思想的果实。 从内心写起,这决定了卡夫卡的创作在叙事方法上的主观性。从主观出 发在这里是一种表现方法,它跟 “自我表现’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可以用来 表现自我,也可以通过自我来反映客观世界。关键是这个 “主观”的作者对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2 月19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2 月4 日笔记。 ④ 卡夫卡:1914 年7 月31 日“内心日记’。
生活的体验和把握的程度如何,他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卡夫卡是有 一定启发意义的。卡夫卡不是革命者,但是个正直的公民和严肃的作家。他 反对专制,反对压迫,不满贫富悬殊,同情下层人民。他的精神痛苦不是一 般的个人哀愁,而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至少,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