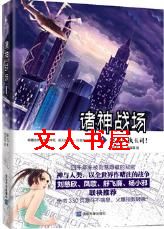诸神战场Ⅱ--旧时的遗骸-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准又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明昧陷入沉思。等她再一次聆听,侍女们的脚步声已消失不见了。确切的说,院子里再无任何人,不过院门口多了几名侍卫。对面厢房内,一概再无呼吸声音;这边厢房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另一个人。那家伙呼吸时快时慢,显然心绪不宁。
审视完毕?
依据是什么?
为何我已经通过?
明昧摸到手臂上。上午第一次见到内侍官时,这里刺痛了一下——是了,有个小小的针眼。
明昧刹那间明白判断标准是什么了。她的心怦怦乱跳,再也坐不住,便站起身走到窗前。
天已彻底黑了下来。月亮还没出现,如霜的星光照亮大地,森林在几百米下毫不掩饰地呼吸、生长。她尽可能把身体探出窗台,举起双手,做出一切顺利的手势。她把这个手势保持了几十秒,又做出准备行动的指示。
有实践三号、四号卫星的双重保证,最迟几分钟内,执玉司就能收到她传递出的这第一份信息。她关上窗,重新回到门前。
咚咚、咚咚咚。另一间屋子里的家伙更加烦躁了,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偶尔还在地上滚几圈。可是明昧的心绪也好不到哪里去。阿特拉斯呢?那家伙整整一天没动静了。矢茵是否还安全?帝启呢?
今天晚上,将是极困难的一晚呢……她闭上眼睛。咕噜噜、咕噜噜,隔壁厢房的丫头又在满地翻滚了,就让她焦躁去吧。自己必须养精蓄锐。再过两个钟头,才真正是折腾的时候呢。
咕噜……汩汩……
矢茵睁开眼。两三米的上方,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碧色。数不清的气泡掠过她的身体,碰到那片碧色,稍稍顿了片刻,而后纷纷碎开,将热气散发出去。碧色由此而不停地荡漾、晃动,却仍然没有一丝消散的迹象。
她蹲着不动,看那碧色摇晃看入了迷。多么漂亮的颜色呀,看得久了,发现也并非完全是翠绿的颜色,还融入了一丝几乎难以分辨的红,一点点儿紫蓝色,一抹橘黄……她看得越久,颜色便愈加丰富而分明。
看出来了,那是水面背后,熔岩洞穴的颜色。
她憋不住气了,双脚轻轻一点,向上飘去,悄无声息地冒出水面。水泛起一圈浑圆的涟漪,以她的头为圆心向外扩展。这个浑圆一直保持到涟漪撞上不规则的岩石,才轰然破裂,纷纷弹回。于是平静的潭水终于变得混乱,那原本凝固的颜色也骤然破碎,似渐渐消融于水。
矢茵长长吐了口气,将湿发抹到脑后。她往后退,直到后背靠上温润光滑的乳石才停下。她闭上眼睛仰头,感受水一颗一颗从发根流下,流过眼眶,流过脸颊,又一颗颗滴落在胸口,慢慢往下流淌……
围绕在潭周围的几十只蜡烛静静燃烧,将这个并不大的洞窟照亮。头顶的岩石离矢茵不过四五米高,它们千万年前诞生在熔岩里,而后被富含硫磺和矿物的水侵润、冲刷、打磨。水留下鲜红、青紫和橘黄的颜色,带走它们的棱角,变成形态各异、色泽分明而又极其光润的模样。
虽然随着火山陷入沉睡,硫磺等物早已被冲刷干净,不过仍然有水从岩石上滴落,叮咚叮咚,滴在潭周围的水洼里,再慢慢流入潭中。潭上方几根乳石垂落到几乎与水面相接的地方,与正在休憩的人儿一道,被四周的光照得透明一般。
并非没有人看到这美得让人窒息的画面。有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偷偷打量,偷偷发着抖。
真是可怕。他活了千百年,见过了无数的人,却从未像今天这般背脊发冷。他探头看看矢茵,就立即缩回,似乎要等胆气凝聚到某种程度,才能再偷看她一眼。
她太完美了。哦,天呐,太完美。那人缩回来喘息时,就怔怔地看自己手心里那根矢茵的头发。天神在上,这根头发的DNA完美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他,必须忠诚于她。
那人每次想到这里,就抖得更加厉害。他脑子里不停冒出要杀了矢茵的念头,可却连这根头发都没勇气扯断。
多少年了?亚特兰蒂斯沉没多少年了?卡拉特克陨落多少年了?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世界再没有神了!再没有神了!她凭什么,凭什么拥有这些……这些他追求了一生而不可得的。他抱紧了头,陷入更深更大的茫然、愤怒和恐惧之中。
要杀她么?还是老老实实俯首称臣?她几乎拥有神一样的DNA,但她知道自己是神么?她手下的那个代理体级别为何如此高?为什么?
昨天晚上,那次可怕的信息,是警告,还是发布命令?它仍然存在,它仍然牢牢控制着一切。但这个人,这个完美的女人意欲何为?难道打算重新启动……打算再一次掀起血雨腥风吗?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恐惧,他痛苦得拼命咬自己残缺的左手,咬得鲜血淋漓,他也感觉不到。噢,这该死的身体!噢,这该死的被诅咒了的命运!
他正在苦苦挣扎,忽然听见哗啦啦的水声,矢茵顺着倾斜的石阶一步步走出水面。那人蜷缩成一团,向黑暗深处退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矢茵走出水潭,一群侍女鱼贯而出,替她擦拭身体,换上衣服。丝质的衣服特别贴身,乳白颜色,用金线绣着只凤凰,从后背绕到胸前,翅膀则在两只宽大的袖子上,只要举起手,凤凰就如同要展翅飞去一般栩栩如生。
侍女们弄好衣服,又要为矢茵盘起发髻。矢茵不耐烦,自己用跟金色的带子把头发扎好,问道:“他呢?”
侍女们一起摇头。
“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
侍女们跪倒在地,纷纷磕头,并不说话。矢茵叹口气,往洞口走去。侍女们不敢阻拦,排成行不近不远地跟着。
她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溶洞。溶洞大小各异,颜色也大不相同。几乎每个洞内都有一潭水,也许有一条地下暗河将它们串起来。无数玲珑秀美的乳石倒映在潭水里,美轮美奂,仿佛天堂。
矢茵可没有心思欣赏。她闷着头走,所幸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岔路,她只管选最大最宽阔的路走,不久来到一扇石门前。矢茵上前推门,她身后的侍女发出一阵惊呼,但仍然没人敢上前拦她。矢茵回头看她们一眼,她们大大地眼睛里流露出恐惧。
“凰王在里面?”
一些侍女摇头,一些拼命点头。
矢茵想起帝启说:“他们不是人,绝对不能以人的角度去看。”便不再理她们,毅然推开大门。眼前赫然大亮。
她屏住呼吸,慢慢走进一座巨大的洞穴。
洞穴高逾六十米,最下方是个直径超过一百米的圆形,往上逐渐收缩,最终的顶点大概只有下方的十分之一大小,如一口倒扣的碗。与之前纯粹天然的洞穴不同,这里的地面被精心平整,打磨得极光滑。人影印在略呈墨绿色的地板上,清晰得如同镜面反射。
矢茵抬起头,立即被光源刺得闭上眼。岛上所有一切遵循着几百年前的生活,可是这里,却悬挂着数十盏亮晃晃的高功率照射灯!
灯光把这巨大的洞穴照得纤毫毕现,矢茵发现沿着洞壁一圈有二十几个石门。石门紧闭,不知门后锁着什么秘密。洞穴里有一种淡淡的腐败的气息,空气也冰冷干燥,与之前湿润温暖的气氛大相径庭。矢茵心中害怕,隐隐觉得这似乎是个坟墓。
她一面警惕地四处看,一面向大厅中央走去。脚踩在地面,一开始觉得冰冷,走着走着,觉得地面越来越热了。
她走到离正中心还有二十米左右,发现中心有一个圆形洞口。嘎吱、嘎吱,单调刺耳的声音从洞里传来。脚下的地面越来越热了,矢茵心开始怦怦乱跳,加快步伐走到洞口,往下看去。
她顿了片刻,慢慢蹲下。她不敢说话,生怕气出大了,帝启也会掉下去。
在她下方十米左右,一只铁笼里,帝启蜷缩成一团,正在沉睡。悬挂铁笼的只是一根拇指粗细的铁链,而在帝启的下方几十米,是无声无息流动着的熔岩。偶尔一块熔岩破裂,炙热岩浆飞溅,似乎离帝启近在咫尺了。腾腾热气冲出洞口,只一会儿矢茵的脸就被吹得又干又热。
一根铁十字四头嵌入洞壁,铁链就随意地锁在铁十字中央。不知是帝启在动,还是被热气吹的,铁笼不停微微摆动,铁链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铁十字一定是精心设计,是竖着的一面宽,横着的一面窄,单凭人的脚根本无法在上面立足。中心离洞壁又超过手臂长度,若没有工具帮忙,根本无法将铁笼拉上来。矢茵试着趴在铁十字上,不行,向上的一面窄得像刀,根本无法近身。
她正打算跳到铁十字中央,两脚分开踩,忽听有人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犯傻——再超过二十斤重量,他就会直接掉入熔岩里。”
矢茵回过头。她的脸被热气熏得绯红,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乱七八糟的贴在脸上——偏偏更增添了几分艳丽。但她的眼光却让那人背心一阵发紧。
“你就是凰王?”
“只有岛上的人称我为凰王,你可以叫我,六十一。”
“六十一?”
“嘿嘿嘿,跟鲁滨逊收留的星期五一样滑稽,是不是?”六十一笑笑,伸出右手。“请,到这边吃点东西,我相信你早饿了。”
“我不,他不上来,我就待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六十一似乎早料到矢茵会如此,手微微一招。矢茵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开了,内侍官当先,侍女们抬着桌子、椅子、各式菜肴果酒出来,就在他俩面前摆开。须臾,一桌丰盛的酒菜就准备停当。桌旁还摆了个精致的炉子,放着壶烧水。
六十一摆手道:“出去,任何人都不许进来打搅。”
“是。”内侍官带着众人叩首行礼,倒退着出去了。
“请坐,呃……”
“我叫矢茵。”
“请坐。”六十一目视矢茵坐下。她不习惯这样长而宽的袖子,一直拢在肩头,手臂上那道伤痕很是刺眼。怎么会呢?她拥有那样完美的DNA,身体却似乎并不能如神祗一样自动愈合。
他小心地把卑微和胆怯隐藏起来,坐下端起酒壶。“要喝酒吗?”
“不。我只是坐坐。”矢茵目不转睛的盯着他。“我的朋友在下面忍受煎熬,在他上来之前,我不会吃任何东西。”
“煎熬?呵呵。”六十一笑笑。他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今天是怎么了?干嘛不停傻笑?这可不好,不能自乱阵脚。要记住,他对自己说,要谨记,神,早在一万三千年前就陨落了。
“放心吧,我敢保证他很好,绝对没有生命危险。你还记得他是如何陷入深度昏迷状态的么?”
“不记得了。”
她在装傻?她下达了一个高级别的休眠命令,不记得了?啊,是了,她在怀疑我的身份。
“我是……”六十一憋了半天,咬咬牙说,“我是第三季中期出生的,你呢?”
“什么第三季中期?我不知道,我刚满十八岁。”
她的眼神闪烁,但是血压和脉搏没有丝毫变化。看来她真不知道——她,也许只是个高级别的触发体吧。
六十一心放下大半,同时生起一种心心相惜的感情。虽然自己的DNA比她低级得多,但好歹成功地躲过了第三季末残酷地低层清理,保留了些许记忆。而绝大多数触发体从出生到死,都不会被触发,永远不真正知道自己的使命。
他为她倒了酒,说:“请。”
“我不喝酒。”矢茵疲惫地摇头。
“请吃点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嘛,不过很显然,饿着是没有力气的。”
矢茵听了,当即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