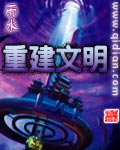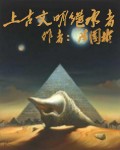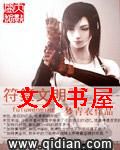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所说的分析者的特殊个人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影响在分析中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可以使你相信,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像催眠暗示那样运用这种个人影响,即运用这样“暗示”因素,来抑制疾病的症状,而且,如果你认为这种因素是贯穿治疗始终的媒介的催化剂,那就是错误的。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无疑是如此。但是后来它就同我们的分析意图相对抗,并逼迫我们采用最有力的对策。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患者的思想偏离分析技术有多远。如果我们的患者摆脱不了负罪感,仿佛他犯了什么大罪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的勿庸置疑的清白;他自己常常试图这样做,却未能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醒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毕竟总是有着某种真实的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可能发现的。
“如果你能以这样赞同患者的负罪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安慰,那将使我颇感惊讶,”这位“公正的人”评论道。
“不过你的分析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究竟对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希望我的话能说得明白易懂,我无疑应该向你谈谈某个在精神分析领域之外无人知晓或无人欣赏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个理论中你将不难推导出我们从患者那儿想要获得和如何获得的东西。我将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向你阐述这一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完善的理论结构。
但是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它就像一个哲学体系那样,是作为这样一个结构诞生于世的。
这个理论结构是我们非常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我们不停地对它进行修改,始终不脱离实际观察,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似乎足以适合我们的目的的完整结构。
就在几年前,我还不得不用别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理论。
而且今天我当然也不能向你保证说,我用来表述这一理论的形式是再也不可更改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科学绝非神灵的启示;一门科学在诞生之后很久仍然会缺乏不容怀疑、不可更改、绝对正确的特性,尽管人类的思想是多么深切地渴望这些特性。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如果你能进一步牢记,我们的这门科学还非常年轻,而且它所涉及的也许是可能成为人类研究课题的最棘手的内容,那么你将会很容易对我的阐述持正确的态度。
不过,要是你没听懂我的话,或希望我作出进一步解释,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甚至想在你开始讲之前就打断你。你说你打算向我阐述一种新的心理学,但是我总认为心理学根本不是新的科学。心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已经够多的了;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就已听说过这一领域的巨大成果。“
我根本不想对这些成果提出质疑。
但是,只要你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不得不把这些巨大成果归为感官生理学范畴。
我们不可能发展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因为这种发展受到一个本质的误解的阻抑。按照当今大学里的教学情况来看,这种理论包含哪些内容呢?
除了在感官生理学领域所获得的那些可贵发现,有关我们的精神活动过程的一系列分类法和定义已经成为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共有的财产。
显然,要提出一种解释我们的精神生活的见解,光靠这些还是不够的。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每一位哲学家,每一位创作家,每一位历史学家,每一位传记作家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关于精神活动的相互联系和目的的假说——每一个假说都似乎多少有些道理,但每一个假说又同样不可靠?
这些假说显然缺乏任何共同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心理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和权威的。在这个领域中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如果你提出一个物理学或化学方面的问题,每一个知道自己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都不会妄加评论。
但如果你想提出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见解,你就必须准备好遇到来自各界人士的评判和驳斥。看来在这个领域里是没有“专业知识”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心理学家。
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称号。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申请当保育员,别人问她会不会照看孩子。
“当然会啦,”她回答说,“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原来也当过孩子嘛。”
“你还声称自己已经通过观察病人而发现了一直被每一个心理学家忽视的那个精神生活的‘共同基础’,是吗?”
在我看来,为了发现科学的真理而对病态的人进行观察,这并不会使这些发现失去价值。
不妨以胚胎学为例,假如胚胎学不能对先天畸形的根因作出明确的解释,这门学科便不值得信赖。我已经对你讲过,有些人的思想总是“自行其事”,不听主观意志的支配,因此这种人总会被迫对一些他们完全不感兴趣的问题忧虑重重。你认为学术性的心理学能够对解释这样的反常现象作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吗?
而且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夜间有过类似的体验,即我们的思想“自行其事”,创造出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使人联想到病态结果的情景。
我指的是我们的梦。普通大众始终相信梦是有涵义、有价值的——它们总意味着什么。但是学术性的心理学从来未能告诉我们梦的意义究竟何在。它根本不能解决梦的问题。即使它试图提供这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也根本不属于心理学范围——诸如认为梦是由感官刺激造成,或把梦归因于大脑不同部位的睡眠深度不等,等等。
总之,我们可以公平合理地说,一门不能解释梦的心理学,对于理解正常精神生活也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它根本没有权利被称作是一门科学。
“看来你已经开始发起主动进攻了,因此你已触及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不错,我已听说在分析治疗中梦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分析者总要对梦作出透彻的解析,并从梦的背后寻找对于真实事件的记忆。
但是我同时又听说,对梦的解析是完全听凭分析者随意安排的,而且分析者自己在梦的解析方法以及根据梦的解析得出结论是否可靠的问题上也一直争论不休。
如果确是如此,你就不应当如此着重强调分析法胜于学术心理学的优势。“
你所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梦的解析的确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假如我的话说得有点强词夺理,那也只是我的一种自卫方法。
倘若我想到有些分析者给释梦工作造成的损害,我也许就会失去信心,耳边就会回响起我们最伟大的讽刺家内斯特罗伊的悲观言论——他曾说 过,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起初看来都像是一大步,其实仅仅是半步而已①。然而,你是否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人们总喜欢混淆和歪曲自己已获得的东西?
其实,借助于一点点预见能力和自我克制,释梦的大多数危险都能毫无疑问地得到避免。
不过想必你也会承认,要是我们一味地听任自己在这样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下去,我就永远没法开始阐述我的论点。
“不错。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要告诉我这门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首先要讲的。
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听一听,我们在精神分析研究过程中对精神器官的结构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你所说的‘精神器官’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关于什么是精神器官的问题很快就能搞清楚,但是我不得不请求你不要问它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这不是一个心理学所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这个问题的冷漠就像光学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用纸板做成的问题一样。我们将把这种精神器官的构成材料问题完全撇开一边,不过空间问题不能撇开。因为我们把这种为心理活动服务的未知的器官描绘成确实像某种器械一样是由几个部件构成的(我们称之为“媒介”),每一个部件发挥一种特定的功能,并且互相保持着一种固定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空间关系——“前面”和“后面”,“表层”和“深层”——首先仅仅意味着一种
①内斯特罗伊(JohannNestroy,1801—1862年),维也纳著名的喜剧作家。——译者注。
固定序列的功能的表现形式。我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吗?
“还不太明白。也许我到后来会明白的。不过,归根到底,你所讲的其实是一门奇怪的心灵解剖学——这对于科学家说来毕竟是再也不存在的东西了。“
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是一个假说,就像科学中的其他许许多多假说一样:最初的东西总是相当粗糙的。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有待修正”这个说法。
在我看来,我没有必要在此诉诸“仿佛”这个已为人广泛使用的词儿。
这样一种“虚构”(如哲学家费英格①所说的)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借助于此所能获得的成绩大小。
不过我们还是接着说下去吧。
只要立足于日常的知识,我们就会发现人有一种精神组织,存在于他们的感官刺激及其对肉体需要的感知与他们的运动行为之间,并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在这两方之间进行调解。
我们称这一组织为“自我”。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不必成为哲学家就可以提出这一设想,有些人甚至尽管是哲学家也能提出这一设想。
但是在我们看来,提出这一设想并不等于对精神器官进行了透彻无遗的描绘。
除了这个“自我”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精神区域,比这个“自我”更为广泛,更为有力,更为模糊,我们称此为“本我”。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予以直接注视的。
①费英格(HansVaihinger,1852—1933年),德国哲学家,其哲学体系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仿佛哲学》中得到全面阐述。该书英译本于一九二四年问世,译者查。凯。奥格登(C。K。Ogden)这部论著在德语国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很可能会反对我们选用这样简单的代词来描绘这两个心理媒介或区域。并不是以朗朗上口的希腊词来给它们命名的。
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不愿脱离通俗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希望的是使这些概念在科学上具有实用价值,而不是让人们拒绝它们。这样做并无好处,我们是被迫采用这个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