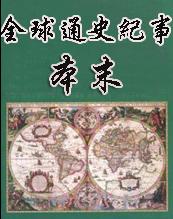全球毒品500年-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自己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的愤怒表现。不但富家妇女用注射吗啡来消除她们的神经痛苦或克制早期歇斯底里,出于镇静的同样目的而且她们的男性医生也给她们注射吗啡。上瘾与性别有关。皮下注射瘾是女性特征。1868年《月亮宝石》中的医生认为自己气质上就易于上鸦片瘾:一些人天生就有女人气质,我是其中一个。” 1880 年在芝加哥对50名药剂师的调查中发现,他们有235个习惯性鸦片客户,其中169个是女性(一般使用吗啡)。
上瘾者的不端行为在19 世纪中后叶受到更多的责备。“如果吃鸦片是恶习”,1851年一位医生鸦片消费者说,“那么它从未把它的受害者引入那些过分粗俗和色情的歧途,这些都会使醉汉成为社会瘟疫。”到19 世纪70 年代,这样的辩解没有多少分量。“她奸诈、狡猾,几乎总是处心积虑得到吗啡,”美国医师贾德森?安德鲁(死于1894年) 描写过一个女裁缝(1841—1871),她最终因注射吗啡的积累作用丧命。“她经常威胁要她自己和她母亲的性命,变得非常难控制”。1875 年苏格兰报道了另一个过失案例。有人看到洛克迈本药剂师的助理让当地的一名妇女溜进柜台,“一个饮鸦片酊成癖者”,她“习惯盯着店里没人的时候,进到店里拿鸦片酊”。她匆忙走进店里,吞下一瓶,二小时后死于误服了干斑蝥。这些恶人有小说版本。在《飞龙奥秘》(The Wyvern Mystery;1869)中,爱尔兰小说家谢里丹?勒?法奴(1814—1873) 勾画了一个备受神经痛折磨的荷兰坏女人波莎?维尔德考斯特。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怨恨、愤怒和残忍自大的报复”。除了大量的白兰地外,她用鸦片制剂消除她的痛苦,因此呈现出一幅“令人疯狂的堕落和残忍的画面”。法奴对上瘾者的描述有时取决于基督教罪孽的概念(她不仅是冷酷无情,也是非常可怕地邪恶和凶猛),有时取决于精神错乱的医学模型(她是狡猾的,野蛮的……有点疯)。
阶级划分同样也存在于对上瘾者的其他方面评判。一位英国医师谴责穷人上瘾者,但原谅那些“社会中产阶级,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求助于鸦片……或回想伤心往事时”使用。然而,中产阶级上瘾者的不诚实臭名远扬。维尔吉?柯林斯在恩格丁旅行时,恐怖”地发现他用光了所带的鸦片酊。他和一位德国朋友“以医生的身份出现,从科伊尔的药剂师那里,后来从巴塞尔的药剂师那里,得到瑞士法律准许的最大量的鸦片酊,以至于到达巴黎后,没有出现柯林斯用惊人来形容的灾难”。冯?C夫人(1842年生)生完孩子后,为治乳房脓肿用吗啡而上瘾,1874 年获许住进德国一家水疗院治疗吗啡上瘾。在那里,她的药量被减少到一个稀释剂量,但是当她被允许与她的仆人在院内外自由走动时,“她晚上偷偷注射和以前一样的量”。这样的事件让列文斯坦坚持认为,上瘾患者得明白,他们必须“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之前,无条件服从医务人员的嘱咐”。他的慕尼黑同事冯?博伊克同样警告说,用吗啡者“不值得信任,非常不顾真相; 特别是当问到他们的毒瘾时”。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8)
可恶的是,医生们倾向于用鸦片和吗啡治他们自己的头疼、失眠和忧虑。长时间工作、半夜被叫醒、令人担忧的病例、苛求的患者、专业傲慢、金钱忧虑和家中龃龉都是造成臭名昭著的医务人员上瘾的因素。“我们的职业代价昂贵,”克劳斯顿哀叹道,每一个乡下医生都不得不半夜翻身起床,跑许多英里疲劳的路,历经许多风雨如磐的夜,(而且)不是因为他的患者比前一天状况更糟。”正是部分由于这样的工作条件,冯?博伊克19 世纪70 年代抱怨说,“大量的吗啡注射器出现了……主要是年轻医生,……干这种有害的事”。例如,1875年列文斯坦治愈了一个医师,他“是为了克服在职业生涯中所犯的错误而自责带来的烦恼和忧虑”开始注射吗啡。美国多数男性上瘾者是医师。保守估计,美国医务人员的10%是“鸦片鬼”,也有人估计是20%。在英国,乡下医生服务范围很大,让人筋疲力尽,据说最容易上瘾。“这种恶习的夺志作用是明确无误的,”阿朗佐?考金斯宣布了一个这样的案例,“鸦片一旦进入,责任感立即消失。不再赞赏真理的道德价值,这个人会刻意地重复撒谎和歪曲事实,表现出最谨慎的辩驳也只会恶化精神的反常行为。”
在医疗机构使用吗啡方面,有许多致命的不谨慎的事例。布赖顿医师詹姆斯?科隆比(1844—1883),1873年被《英国医学报》批评,因为他发明了一台吸入器,用于自己吸三氯甲烷气:自我吸入麻醉剂导致睡眠的方法……发现有害、危险,并不幸地带来致命后果。”然而,科隆比被证明是一个难以对付和足智多谋的劝诱者。他哀叹“注射器的昂贵和纤巧”妨碍较贫穷阶级的人皮下注射吗啡,设计了一种便宜的皮下治疗方法。他给细丝线涂上一层吗啡,用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口子,在里面拉丝线,让吗啡粘在开口的皮肤下。科隆比1875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疼痛:原因和疗法》(Pains:Its Cause And Cure)。他发现吗啡有致命的吸引力。他死于过量注射吗啡。据说他是在做了手腕手术后,用吗啡保证睡眠。《柳叶刀》评论说,尸检显示,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要禁止专业患者用一种致命药物自医,而且要小心不要让他得到这种药”。医生们的妻子常常死于粗心大意使用吗啡。卡莱尔一名年轻医生的妻子安妮?麦克劳德(1848—1873 )的死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她连着几个夜晚照顾生伤寒病的儿子们。最后当她有机会休息时,因紧张过度而睡不着。她丈夫因此每隔三个多小时用葡萄酒杯给她喝吗啡。然后她进入昏迷状态,如此令人担忧,麦克劳德博士寻求其他的医疗援助,但所有挽救患者的努力都失败了”。
一些英国医师认为,禁酒运动增加了鸦片在农村地区的使用,驱使穷人使用廉价的致醉替代品。但是,在美国“禁酒”地区,没有证据证明鸦片上瘾或滥用乙醚升高。虽然美国妇女喝酒不合礼数,但礼数公开或悄悄地被边远地区的乡下妇女或长期与丈夫分离的海员们的妻子打破。尽管强调仪态,一些时兴的妇女在酒精或吗啡里找到防御办法,抵御她们周围的白热化竞争。上流社会的压力太明显了。“作为个体,人们足够好,表现得亲切和有礼貌,但彼此的嫉妒和辱骂却惊人,”达弗林蛳艾瓦侯爵夫人(1826—1902)1874年参观纽约后记载说,“每个美国女士似乎都为她最好的朋友感到羞愧。的确,你经常被弄得感觉好像你住在仆人房间里。”有毒瘾的人当然不都是神经紧张的妇女、富有的浪荡子、贫民窟的居民或医院里被毁的医务人员。在这个期间,金融投机商也与毒瘾有关。根据1871年的报告,华尔街经纪人抵抗住“一种兴奋; 黄金热;用的是另一种兴奋; 刺激的鸦片制剂”。B夫人,一个25岁的纽约人,定期造访证券交易所,她把吗啡注入直肠。“一天要注射几次,在国内、国外都一样;经纪人事务所里的空间,或一条偏僻街道的一个角落,任何偏僻的地方都是注射之处。”她所有戒毒的努力都失败了。
安斯蒂认为,某些人气质上易于上瘾。在《兴奋剂和麻醉剂》(Stim…ulants and Narcotics,1864)中,他区别了两类使用者。有“不谨慎的人”,他们使用鸦片制剂止痛或治病,并且被说服,增加药量会增加效果。这样的事例特征不是“喝醉的欲望”或为了忘却;相反,真正浪荡子”喜欢陶醉和热衷逃脱“所有现实生活环境”,进入“傻瓜”的天堂,充满肉体快乐的幻觉。在欧洲; 直到1950年以后,安斯蒂的“不谨慎”类别——由于治疗的原因染上鸦片瘾的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浪荡子”。到20 世纪末,后一类在西方世界的毒品问题中占支配地位。安斯蒂判断,浪荡子增加酒精、鸦片或古柯的消费量,因为他们“低劣的道德品性喜欢非自然的欢乐,这种欢乐现在只能靠这样的增加获得”。他认为这样的低劣品质是一个人自身性格固有的,不取决于毒品的渐进作用。浪荡子“要么生来就有明显的玩乐倾向,要么特别对某些外部印象敏感”。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9)
这种致瘾个性的纵欲理论忽视了19世纪关于毒瘾一个公认的特点:一些战争中战斗人员的易感性。尽管19世纪70年代鸦片瘾与妇女有关(美国鸦片和吗啡上瘾者的60%以上是女性),这个问题还被看成是“军队病”。病、伤战士和退伍军人,给他们开药不注意用量,使他们用了之后上瘾,或者发展到像战斗中肉体受到折磨一样,因为情感受到折磨而依赖这些毒品。正如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于让毒瘾支配他们的生活一样,一些人同样发现比其他人更难从战时的情感痛苦中恢复。上瘾者的行为(与他们上瘾的原因比)不完全是受生理需要的支配。战斗压力倾向和管理在个人之间同样是可变的。由于越南战争,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造了一个词,“伤后压力失调”,描述受伤人的行为。这种行为,精神病医生会称为神经官能症,外行会认为是自暴自弃或失调。这没有任何新意。战斗场面造成的情感损伤,19世纪就已经明确确认。19世纪20年代期间,英国政府对从法国战争中退役军人的问题做出反应,他们在乡下漫游,好斗、无礼或怪癖。退伍军人向妇女展示他们令人作呕的伤疤或其他身体部位的习惯,1824年《反流浪法》为此作出规定,任何人恣意、公开、淫荡和淫秽地暴露自己,旨在欺辱女性……将被视为歹徒和地痞”。
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军队对俄国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显示出战争造成的情感损伤。1854年,在英克曼战斗中,8500人的英国部队,四分之一以上的士兵丧生或受伤;俄国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总数42000人中的大约11000名士兵。爵士乔治?希金森将军(1826—1927)在近卫军一团参加了那次战斗。20年以后,有人向他问起英克曼。“他对那场战斗记得很少,”问他的人记载道,当他们走回来,加入失散的连队以后,他只记得战友们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了一个晚上。”在另一段讲述中,希金森描述了英国的总司令剑桥公爵(1819—1904),在英克曼之后“几乎感动得落泪”。他还回忆到,圣?吉尔曼斯伯爵(1835—1911)站在他兄弟的尸体旁,“痛苦得一动不动,不顾危险,暴露在枪林弹雨中”。后来,当“饥饿的战友”涌入希金森的帐篷,一整天神经如此高度紧张,我们竟然禁不住笑起来”。福思勋爵(1834—1861)用鸦片酊自杀,也许可以算作克里米亚战争神经伤亡人员。他从部队退伍后,精神崩溃,年仅20岁。他情妇死后,痛不欲生,喝了四分之三品脱的白兰地和寻死地吞下半瓶鸦片酊。
大约400万部队参加了1861 年4月到1865 年4月同盟军投降的美国内战。在战斗中,或因伤病,北方大约损失了36万名士兵,南方损失了万名士兵,估计有万名士兵受伤。平民和他们资源的介入,就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