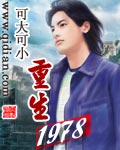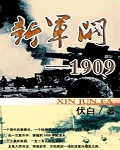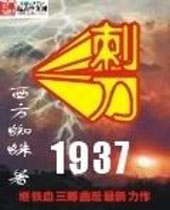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只有被驱逐者自己才能判断驱逐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看历史》:那些被驱逐者后来的命运如何?
莱斯利·张伯伦:大多数情况下十分艰难。随着希特勒上台,那些在德国的被驱逐者,尤其是犹太人,生存更为困苦。从很多方面来说,来到法国的流亡者的境遇是最好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大的流亡团体,而且他们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可以办一些期刊杂志。但是这些援助在1939年大战爆发之后就结束了。即使是那些能够经济自立的流亡者,也因为离开祖国,受到孤独和悲伤的折磨。大部分人在离开时都存在幻想:他们不久就能回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看历史》:但是有人说这次驱逐行动,对被驱逐者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因为流放者获得了自由和尊严,逃脱了此后苏联的种种政治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取代了巨大的成就,保存了俄罗斯思想的火种。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莱斯利·张伯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赞成这个看法。如果他们不被驱逐,他们可能无法在苏联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驱逐对这些被驱逐者是一种幸运。一旦他们被西方接受,像别尔嘉耶夫和弗兰克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肯定能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俄罗斯文化。而且他们不仅站在外面看待俄罗斯,也批评西方,这把他们的著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不仅仅是二十世纪重要的俄罗斯批评家,也是西方批评家。这被驱逐者中,有《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著名的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也有流放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索罗金,他日后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但是,我认为只有被驱逐者自己才能最终判断驱逐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 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
《看历史》:您说“‘哲学家事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为什么您认为这个事件具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
莱斯利·张伯伦:这是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不仅思想被禁止,而且持有和代表这种思想的人也被驱逐出国。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有放逐诗人的要求。但是俄罗斯人将之变成现实。这个国家似乎经常比西方人先行一步:漠视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在二者之间建立系统的噩梦般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其它时期,在其他国家,也有群体和民族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或驱逐出境。但是我之所以称这个事件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这个事件中的被驱逐者是来自不同派系的*者,他们一并被列入统一的名单,由一个最高的政治领导层监管。这是与柏拉图的设想最接近的现实。当然,在你们中国,也有你们自己的清理知识分子阶层的类似历史。
《看历史》:你不仅是思想史家,也是一个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哲学船事件》就是一本出色的非虚构作品。在中国,非虚构写作正变得越来越热。您能谈谈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学院派历史研究的区别吗?
莱斯利·张伯伦:我受过学术训练,然后做了九年记者,但一直想写小说,所以对我来说,以畅销书的方式表达我的兴趣似乎是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我试图把把学术的诚实和讲故事的快乐结合起来。
在我写类似“哲学船事件”这样的故事时,我在个性和原则之间不断倾斜。可以说,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的观点汇合了,这种汇合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虑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想法和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流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对表现时代、生活、地方和国家的小说不满意,反而从“真实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阅读的快乐。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偏爱“事实”多于想象的时代,这有好处,但也有缺点。我个人希望能写更多的小说。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在其他时段内会不断重获生命的人物活起来。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大国兴亡谁人定——读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树增
近代中国的沧桑岁月,缠绕着太多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奋争和苦难,激情与梦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国离乱与民生沉浮。
然而放眼全球范围,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中,为何康熙皇帝仁政爱民却使大清停滞不前,彼得大帝凶暴治国反而让俄罗斯一飞冲天?为何慈禧太后殚精竭虑却“越帮越忙”,维多利亚女王甘居幕后大英帝国却高速发展?为何明治维新使日本一飞冲天,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翻开青年军旅作家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一幅幅风云画卷荡气回肠,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浩叹深思。
这是国内首部通过中外人物对比解读大国兴衰命运的著作。作者试图立足中国,兼顾全球,把“天朝上国”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审视分析。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是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好的历史学者,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制度探讨。这本书写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将相但无常见的官经匪气,写到才子佳人却无宫闱秘事。王龙笔下对比解读的每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或英雄末路,或一飞冲天,或功败垂成,或光芒四射。他们个人际遇无不投映出国家民族的命运,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归宿。
作家搬来一面面“西洋人物镜”进行对照鉴别,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张X光片,反思华夏数千年传统中的制度灾难和文化痼疾,为中国历史寻找普适性的世界性座标。王龙写道:“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从小细节处看大关节,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王龙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情境里,将近代中外名人还原为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像,无论写到慈禧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见我们惯性思维中穷奢极欲的暴戾和“欧洲的祖母”式的慈祥。从中你会看到一个多才多艺的慈禧,也会看到一个贪婪恋权的维多利亚女王;而同为博学多才的一代明君,当康熙大帝在“红墙深锁的宫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大帝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他挥动野蛮的鞭子加速把俄罗斯赶向文明”。而对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成败得失,王龙则从他们在个人出身、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其事业兴衰的必然规律……正是这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清中西英豪的风云对决,大国浮沉的拍案惊奇。
该书所作的个性化历史结论未必不可探讨,这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进展,东西方的冲突和融合势必更加凸显,这种针对中西方比较的历史文化探讨也必将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因此看来,这本书的生命力将是长久的。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力长久的书,定是本好书。(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1)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看历史》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草木篇》的小诗而触犯天颜,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于全国的右派成为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饱受屈辱和磨难的悲剧人生。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须有的株连而成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剧。
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诗案”。
而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四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态度点到其诗其人,更使其成为当代史上的一桩奇案。
至今,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满怀人生梦想的青年诗人流沙河,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幻想”的平静老人。这是他第一次追忆“草木篇诗案”。其中许多情节从不为人所知。例如其父亲被新政权枪决,冉云飞说,他与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对于父亲的死,沙河从不提及,1981年的《自传》里,甚至说,“是应该的”!可见创深痛巨,无以言表。
本文据录音整理而成,并尽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语原貌。为了方便阅读,加了小标题。另需说明的是,个别地方根据今天的语境有少许删节。
■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19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1951年。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都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信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丘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txt电子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