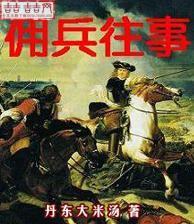往事亲历-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7)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抽了两包烟。我现在想女孩子流眼泪,男孩子的眼泪都变成汗了。
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先看到了妈妈。那是六月份,北京很热,妈妈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因为她的身体太弱了。妈妈一边拉着我,一边拉着哥哥,那时候我妹妹黎明还在陕西插队,没通知她。姐姐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过去,病房两边的门都打开了,病号在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知道了,都在看。妈妈就使劲捏我的手,不能哭。
从那一刻起我就没眼泪了,好奇怪,就没眼泪了。到了病房,床上就是一个白被单压在爸爸的胡子上面,头发也梳过了。一看我就知道是他,但什么都不能说。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负责记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们都很吃力,确实很吃力。后来妈妈很冷静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吧?就带着我们出来了。
(贺晓明哭了……)
贺晓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在贵州东南部某县教育局工作,后到山西卫生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北京,调任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
威严的父亲
贺黎明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从懂事以后她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
记者:您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懂事以后您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跟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知道您父亲习惯留胡子,非常威武,您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对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8)
贺黎明:我父亲本身结婚就比较晚,父亲和我妈妈相差了25岁,我妈妈那时是延安县长,也是组织介绍的。他们一天到晚地打仗,南征北战,根本没时间找对象,当时是彭真同志介绍的。
父亲留着小胡子,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允许留胡子的人,非常威武。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人。但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见了他,有的时候说话,舌头都有点僵硬,打不了弯。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的父亲?他威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很亲切。
比方说,我15岁的时候入了团,我妈妈就很高兴,就告诉老爷子说咱们“幺女”入团了,老爷子一听就很高兴,把我叫到一边去,拿了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说,这是你入团的一个奖励,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我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搞物质刺激。我们老爷子就笑一笑,家里气氛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家孩子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我妈妈名字后面有一个“明”字,当时毛主席就说,将来你们要生一排小龙,再生一排小明。这样生到儿子就叫“龙”字,生个女儿就应该叫“明”字,所以就叫晓明、黎明,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人家解释,我哥哥贺鹏飞的小名就叫小龙,我姐姐的小名叫小明,我的小名叫幼明,意思是我们家又来了个女儿,延续我妈妈那个名字。
记者:您看到您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说话做事都很融洽,能通过什么事情表现出来吗?
贺黎明: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彼此互相关心。我妈妈脾气比较温和,性子比较慢,处理问题也比较周全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我爸爸是我们家的司令。
如果我爸爸生气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我妈妈当时不会说什么,等到我父亲气消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就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做爸爸的思想工作,在跟我爸爸聊天。妈妈都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和我爸爸谈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过。在家里,爸爸他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个好爸爸。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夜里我给弄醒了,我眯缝着眼,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比较重,在笨手笨脚地给我盖被子。妈妈出差了,他来给我盖被子。我没出声,假装睡着了,因为我一醒了就证明他失败了,你盖被子都给我盖醒了。因此我就没出声,其实当时心里很感动。
吃饭时爸爸要求我们不许掉一粒米粒,饭碗要吃干净,什么菜汤啊,菜叶子啊,绝对不可以掉在饭桌上。我们家除了自己家的成员,还有烈士的孩子,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孩子,吃饭时通常是两桌。我们吃完饭自己收拾碗、盘、勺、筷子。谁吃完,谁就把自己的拿走,桌子上干干净净。
爸爸讲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28道程序,你们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1965年,我爸爸主持国防科委工作,那一年他带我们去东北,我想就是去玩。夏天去东北挺凉快的,是个好事。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天天跟着他一起参观军工厂、飞机制造厂,天天开会。爸爸要求我们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听人家给我们解释,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走神,他胡子就翘起来了,拐棍就要上来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9)
这个拐棍是用来敲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威风,就连我们家的动物都知道要怕谁,要欺负谁。比方说我们家一般都会养一些狗、鹦鹉什么的,还养过猴子,这些动物见了他都很害怕。这就很奇怪,父亲从不喂它们。我们家的狗见了他就会趴在地下,猴子见了他就会献媚,拿着小爪子去勾他的拐棍。但是那些狗、猴子见了我就会欺负我,就冲着我呼呼呼的样子。只要父亲一散步走到那儿去,它们都规规矩矩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而在家里却又这么让孩子喜欢,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吗?当时去你们家的这么多孩子和您父亲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贺黎明: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其实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哥哥、姐姐还有我,但除此之外我们家还多出来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人,一些老同志的、烈士的子弟,还有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来,就住在我们家,所以非常热闹。
我记得当时罗荣桓同志因病去世以后,我父亲对他的儿子罗东进很关心,经常会问一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张鼎丞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邻居,我父亲都会问他们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情况怎么样,在政治上是不是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都很鼓励。包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父亲都会替他们去做,就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他都会想到,都会去安排。
我们家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就在工作人员的食堂里。周边住的有罗荣桓元帅家、张鼎丞一家,还有刘伯承元帅、陈老总、罗瑞卿,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他们几家都住在那个院里,还有彭真家。一到星期六,这些孩子们都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晚上演什么电影,到时候大家都过来了。
业余时间大家会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无拘无束,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玩累了,我就会跟林月琴妈妈说:林妈妈,我今天在这儿吃饭了。等于我既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也同样是这些老同志的孩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包括现在就像宋任穷的爱人,还经常来看我妈妈,他们的孩子也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注重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孩子们不怕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去北戴河,我哥哥他们那一辈的,包括像万里同志的儿子、陈老总的儿子,他们一起踢足球,跟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在一个足球场上,无意中开始对垒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孩子很傲慢,觉得他们肯定技术要好,本来是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比赛。
他们踢完第一次球以后,回去跟我爸爸讲,说他们今天是跟苏联孩子在一起踢球。还约好了下一次进行一次正式的比赛,老爷子就对他们的比赛很认真。
我记得那次正式比赛的时候,除了主席不在北戴河,在北戴河的这些常委都去看了。我们都属于拉拉队,全场给他们助威,那场球好像是踢平了,没有赢人家。但是我们敢于去拼搏,在竞技场上不能输给外国人。我父亲就要求我们要勇敢,要勇于克服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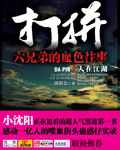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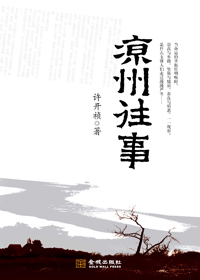

![[HP]霍格沃茨一段往事封面](http://www.xntxt2.com/cover/18/188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