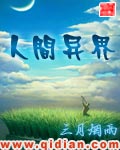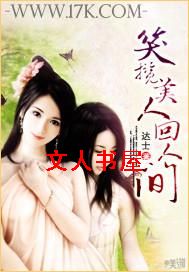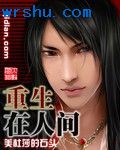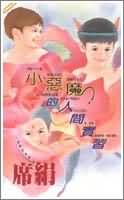�˼�ʻ�-��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Ҷ�ڷ�������ڶ������١����õü��ã��Ѻɻ��ڷ��е���̬��Ϊ����ı����˳������൱���ʡ���������ϸ�ں���д��������Ȼ���ܰ���۲�ϸ�£������������������ڣ���ҷ緶��¶���š�˳��˵�£�����Ӧ��������һ��СС�ı������״�Ӧ�ǡ���Ļ�ڡ����ǡ�������
����������µĺɻ�������д�ɻ����˵ĸд����������Լ����軨�Ը��ԣ�����������Ǹо��Ͼ�ʧȥ�˺ɻ�ԭ�еı��档���Ѿ�����д��������д���ˡ�����Ȼ�������������Ӱ�ӣ������ľͲ��ǻ��ˣ�Ʒ��������ȻҲ�ͻ�����С��������֮���ˡ����ܰ�����µĺɻ���ȣ�������д�ɻ����Կ۵��ӽ�д�ģ���ʯ��д�ɻ��������۵��ӽ�д�ġ��ܰ��忴�����Ǿ��DZ���̬֮�ĺɻ��������������ɻ�������λ��Ц��Ȼ�ļ��ˡ���Ҫ���ֵ����ݲ�һ�������˶����������ϵIJ��졣�����ⲻ�ںɻ��������״���������ʱȽ���ʵ������ʮ��ǡ����
�����˼�ʻ�֮��ʮһ
����������������Ӧ�����������������ʣ���ע�ƣ�����ҹ�������������֡���ν�����������ڸ���Ҳ��ë�ӽ�ν������������˷��ԡ��������λ��������ܡ����⡨���֡��������壬��Ц��Ҳ����
�������루1109��1180�����ִ������꾩�ˡ����δ��ˡ������У�Ϊ������֪�͡�����������������ͬ��˾�����ٱ�����Ȫ��ʹ����鳼����Ԩ���Ϊ�飬Ϊ�˲��ݣ�����ʷ�����롶���ɴ����С��ʶ�Ӧ��֮�����������������������ġ�
���������������˽����´�Ҳ���ϻʴ�ϲԻ���������´ʣ�������'���'�£���ν���档���ͽ���������ެ�ޡ�ˮ���롣����ͱ�յ����һ�����ع�����ҹ���������������ɡ�������
����������̣����������͡�һ�����¡���ˮ孺��˲���������������𡣡��������ϣ�һʱͬɫ��С�����ѵ���������ϣ�����͵�����ס���
��������˭�����ţ�������Ϸ��һЦ�ɳվ�������Ⱥ�ɸ��紦������ˮ�����ڡ��ƺ����壬ɽ��Ӱ�������䴵��ѩ�����������ǧ����ȱ��
ë��˵����������˷��ԡ�����ָ�����������ˣ���������ʽ������֡���ʵ������ָ����������ë���������壬���˽⡨���֡���������������壬������ȡЦ�ˡ�
��������Ӧ��֮������������仪����ȴ�����Ϊ�ʵۻʺ�蹦�̵´�������������������ʵ�У���������ļ��١���ס��������ѻ����ݡ�����ˮ����ݡ����Ǿ�����棬����������������ע��˵���ϻʴ�ϲ�����ͽ���������ެ�ޡ�ˮ���롣����ͱ�յ�����ƣ������Ե�֮�������Ա���һ��С��������δ��������֮���ᡣ
����ǰ������˵����Ӧ�ƴʡ�ϲǨݺ�������ϻ�����ǿ�̳С����ض𡷣����Ǻ�̧��������ˡ������ٴγ���Ӧ�ƴʣ�����Ӧ�ƴʿ����������DZȽϹ�ע�ġ�Ӧ�ƴʺôʼ��٣�����������Ҳ���ࡣ���Ҽ����Ǻôʣ�ҲԶ������Щ���Ҽ��������˼�ʻ�������ôʶ���ȥ�ˣ�Ӧ��֮���������Ų��Ϻŵġ���������������ἰ����Ӧ��֮������Ȼ�仹���Գ������ڵ��ƴ�ͳ��������
�����˼�ʻ�֮��ʮ��
�������Ž���˸��֮�ߣ������ʯ��ϧ�����⾳���������ʾ�������֮ζ������֮�졣����ڶ��֡���־�������֮����ּң����δҲ����
��������������������������Ȼ��Ը�������ס�����˵���������⾳������������ʵ���ϰ�ʯ�����⾳���Ǻ������ġ���ʯ֮�ʶ��Իް�����֮�����������į֮�顣�硨���������ǧɽ��ڤڤ��ȥ���˹ܡ�������ʮ�������ڣ����ĵ����������������������軨����������ϯ������˥�ݳ��̣���ѻ���գ���ɳ����ƽҰ���������������ǽ��ѩ�ϣ�����ֳ������������廷��ҹ�����������˻��Ķ����ȵȣ�Ī����ˡ�����ּȤ֮���ʯ���������˵������Ƿȱ�������෴����ʯ����������Ϊ��̵ġ��������Ϊִ����һ�����龳����ʱ��ζ�Ƚ����ԣ������⾳���ֺܶ�ʱ����ڿݰ����������������ӵ�����������Զ֮�¡���Ӧ�þ���������˵�ġ�������֮ζ������֮�졨������ּң����δҲ��֮��ָ�ɡ�
�����˵��Ը���������ͬ�������ͺ�ϲ�����⾳��ȻҲ������ͬ����ʯ�ʻ������ܲ�����ϲ���ģ���������ν�������ʣ������ǡ��ˡ�����֮��Ϊ��ң����������걻�˳������������ĵ��������Բ�ϲ��ijһλ�ʼң���������Ӧ��Ҫ�еġ�
�����˼�ʻ�֮��ʮ��
������÷Ϫ���δ������ɣ������ɡ�����ԭ��ɾȥ��������ݴ�����´��ң����䲻ͬ��Ȼͬʧ֮��dz����ʱ��ʹȻ������ŷ�����Ҳ���������ܶ�������𭣬ʵ�����⡣��
����ʷ���棨1163��Լ1220�����ְ��䣬��÷Ϫ�����ˡ���Ϊ̫ʦ���������������������б���ʧ�ܱ�ɱ��ʷ���汻�������š�ʷ��������ӽ��Զ�����˫˫�ࡷΪӽ�������������ᆱ�����ɣ������ִʵ���̫�������粻�ߡ�������÷Ϫ�ʡ�һ����
�����Լ1230��Լ1291������ʥ�룬����ӽ���������ɣ��ֺű�ɽ������ɽ�ˣ�����ˡ��������ȳ���Ԫ��Ԫ·ѧ���������ﳤ��ӽ����õ�ʣ�Ϊ�峣�������Ƴ硣������ź����������Թ֮�����桶���⼯��������������ɽ�˼���������ɽ�ָ�����
�������ܣ�1232��Լ1298�����ֹ������Ųݴ����ֺ���ի��ƻ�ޡ���ˮDZ���������ˡ�����עɽ�ˣ��漮���ϣ���Ԣ���ˡ���ĩΪ���������Ԫ���ˡ���ʸ����Ͻ������ڴʴ��ž��£�������תΪ������ʡ�������Ӣ�������У����ơ����������С��ݴ������������ֱ������δʼ�������ôʡ���
��������ƽ��Լ1205��Լ1280�����־��⣬һ���ٺ⣬����´�������ˡ����δ��ˡ�
������𭣬�չޡ����ߺ�������ӹ�š��ܶ����ܴ���Ϊ��֮�����������ɶ�õ����š�
�������δ��˵ķ������������һ�����š��֡����δ��˶�ѧ�ܰ��壬�����¾����Ĵʷ硣Ȼ���������ɲ���߾���Dz������ܾ������ᣬҲ�վ��Ӳ������˶�������������������ϣ��ָ��ο�����ѧ���Ĵ����أ�����ǰ����˵��ʫ����ѧ�ġ���Ϊ�������ֺ�����֮��̫�������������Dz�ѧ���桢���˱�Ϊ����ּ��ٵ���Ľ��ݸ��˴�����ϲ��
������ĩ���˶���糪�ͣ���Ȼ�����־侫�������ɺ�г��Ȼ�������⾳��С��������ߡ�����֮����������һ�౯�����ʣ��㷢����֮ʹ��������ĩ��Щȱ������ʵ�е�����֮����������һ�����������ǻعⷵ�գ��ʻԻ��Ӻ��ڴ����������꣬�վ����仨Ʈȥ�������������������������ղ�������֮����̳�������������ȣ����˲�ʤ���ꡣ
������������������������١����δ�Խ����Խ�Ե�ֻ���������ɶ��������龳����ʯѧ���ɣ�������ѧ��ʯ��ԽѧԽ�������ʿ�����������Ӵ�úÿ���������ն���������Ĵ�ʵ��������Ϊ�ۡ�
��������ԭ��ѡ����ɡ�ɾȥ�������������˲��У�������Ϊ��ʺ�����ת���������࣬�������֮������������֮�����ʵ����ά����֮��Ҳ������ˣ���������֮̾�Ž�����ɡ�
�����˼�ʻ�֮��ʮ��
����������ʲ�ϲ���������ֲ�ϲ�����ϡ�ż����Ϸ������ˮ������ӽ����ʷ��³����ϣ����������֡�ӽ���ð�ʯ�ϣ������������֮�⡣Ȼ��֮�����ⲻ���ǣ���֮�����������ʳ��ҡ���
���������״�����˵�С�������ˡ�֮�⣬Ҳ��������ԭ�����Խ���һ�¡���ˮ����������Ͳ����Ƚ��ˣ����ĺܿ�ͻ��ᵽ����ʱһ����Ƚϡ�
���������������������ά�ġ������֡���
�����֡�������꣬���Ź��������Ŵ��֮�á����ݱڼ�������������Լ��ͬ�������ڸ��ߡ������ȳɣ������������ǻ����䣬�������£�������˼��Ѱ��ôˡ���ж���Ϊ��֯���ƶ�����������������ʮ��Ǯ��һö�������Ϊ¥������֮��������
������������������������˽�¶ʪͭ�̣�̦��ʯ�������������������������ߡ���˼�����ߣ���Ѱ���̡�������ɽ��ҹ��������������
���������ִ����꣬Ϊ˭Ƶ������������ƣ����ӭ��빬���£�����������������ʫ���룬Ц������ƣ������Ů��д����˿��һ�������ࡣ
���������֡�������ά
�����������Գ��K��������ų��է�����ף��������ˡ����뻭����������ߡ��м�����˿���������̡�һҹ���ã����������ǧ����
������ͥ������ꡣ���ϳǰ��أ���Ժͣ�ơ����������ã�����������г�����������á�롣�����ȴ�������Ҷ�Ů����ʶ���������˴��¿ࡣ
������ʯ��ƪ����������Ϊ�����������������һ����������Խ�˳��ŵ�ʱ�⣬�������й������������ҹ�֮�ޣ�ֱ�������顣
������䡨��������������������˽������ɼ����ţ���������������������˽������˹���Һ���������˼����֮������ij�����ȴ����˽������ڶ������dz������ᣬ�������š���¶ʪͭ�̣�̦��ʯ��������������������ͭ�̣�ͭ�������ף�����ʱ���ϵ����Ż����������⾮�ߣ������š���俴��ƽ������д���������ӱܣ���ʵ�ǰ�ָ���ɱܣ�ҲΪ���桨˼�����ߡ������·��ʡ����������ߡ���������Թ���ߣ���ȴ�����˿��ߣ�ֻ�ܶ�������һ��˽��˾��ϳС�˽����¿������ߡ������������������˼�����ߣ���Ѱ���̡�������������֯��������ʱ�ܶ�Ů�Ӷ��ǰ�����һ�������ߵij���֯����ɴ��˼�����˰ɡ���֯������ֵ��DZ��˶����������ɴ�֯����ҹ��֯�����龳���ɵú���Ȼ������ͻأ֮�С�˼������շת���������������ߣ�ֻ����֯������������ɽ��ҹ����������������������֯�����ϣ��������������ϵ�ңɽԶˮ������Զ�������ˣ�˼��֮�������Ӳ����ܲ����������ҹ����ˮ�����ϣ�����һ�ˣ��µ����ߣ�������Զ����������������������δ֯�����ֳ�ٽ��������Ҳ��ֻ��˼�������������õ��ɡ�����ĩ��������dz���д�ȴ���
���������ԡ������ִ����꣬Ϊ˭Ƶ������������ƣ�����ʣ����ת��֮����߱ʷ�����һת����֯��������Ů�������ڵ����⣬��ת������������֯�����Ǵ�����һ�����⾳�Ĺؼ����������꣬˼�����˵��ֺ�ֹ��֯������һ�˶����أ���ס���ҹ��衷���ƣ�������һƬ�£�����������紵��������������顣����ƽ�����˰�Զ������֯�º͵��¶����˶������֮̾��������֯�»��ǵ��£����������һ�ֱ���֮�ࡣ����ϳС�ҹ�����������������¿��������������������µƺ�������簵�꣬��һ�����ij�������Ϊ˭�뵷�µ�����������أ������뵷�����������ţ����Թ¶����ȣ���˼�����������ӭ��빬���£��������������������ǡ����Ĺ�������������֮�ˣ�������û���أ�����е�Ǩ���